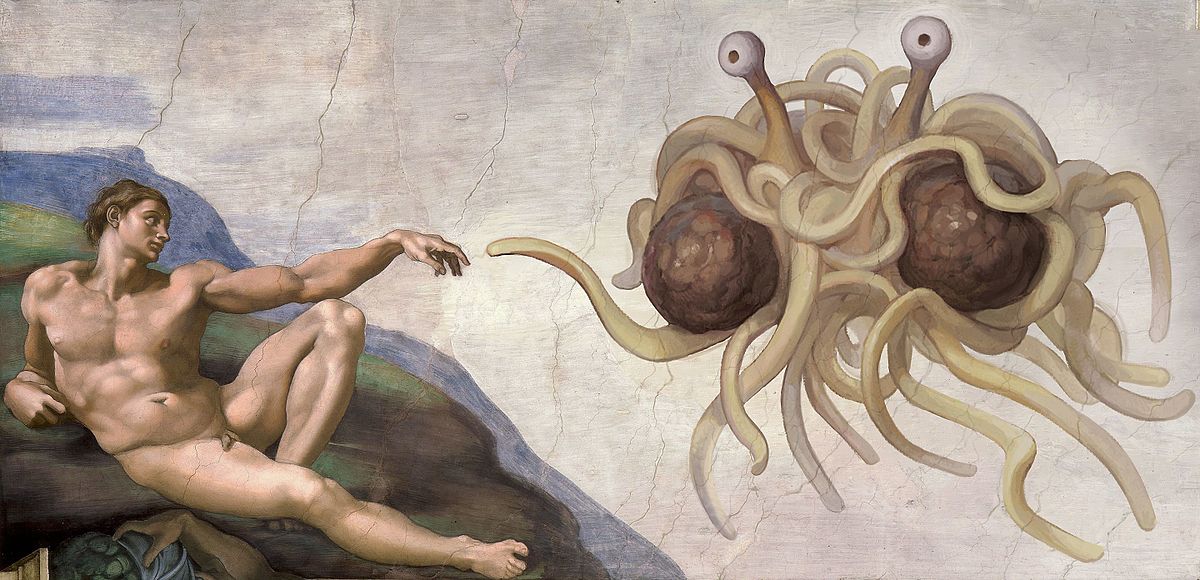每次感觉等国已经没有什么能让朕惊喜的了,等国就身体力行告诉我:能偷着乐的还有的是呢 ![]()
QT: [https://o3o.ca/@secretgoldfish/108640022360676343]
众姐妹们,真的…但凡有能力,赶紧跑!!!不要回头!!!
转自wb用户三禾君:【在论坛看到一张线上监控识别讲座的截图,搜索了一下案例为腾冲市(云南省)。
女人在街边驻足1分钟、夜间和异性交流超过5秒、多次在同一地点出现,就会被算法判定为站街女。】
官方鉴你是不是妓女吗?且不说它有何种资格、凭什么?你国有这个技术,为啥不拿来识别公开场合暴露、尾随、抢劫、性骚扰的男人啊!退一万步,你怎么不识别嫖客呢?
【经人提醒,原链接有追踪标志 删了】
#通勤干点啥
时差14# 育儿劳动 性别 社会政策
其实关于抚养、母职的讨论零零散散也看了不少,但每次听学者谈自身经验、谈理论视角总还会有新的感受。
除了谈得比较多的生育/堕胎的法理自由vs实践自由、母职惩罚、母职的浪漫化问题,母亲自身心理上丰富多元体验同样需要关注到。张晨晨谈到她在看顾幼儿时感受到与世界的“isolation”,这不是简单的全职妈妈与世界发展上的脱节,而是母亲在囿于家庭时与社会“失联”的感觉。一位女学者谈到她主动选择休比例较高的产假,因为不想缺失孩子的成长——无法否定的是,有些母亲是主动自愿,甚至热爱参与抚育过程的,而这部分声音在女权话语强势的场域似乎显得不太正确。
也可以看到,全世界对母亲的支持仍然远远达不到平权的程度。张晨晨身在丹麦,当地福利体系对母亲的支持很多,尤其是发达的幼儿照料机构。但她仍然会在“生育之前的体检入医保、生育之后的体检自负”这样的细节中体会到母亲的需求、母亲的主体性如何被忽视。而哪怕是男女可以同休产假,母亲的产假内容与父亲的产假内容也和不可同日而语。而在中国,中产阶级女性虽然可以通过购买育儿嫂/保姆来部分减轻负担,但仍要付出大量的“管理劳动” ,对保姆的面试、把关几乎都是由母亲在负责。抚育商品化后“科学育儿”的话语也极大程度贩卖了焦虑和增加了母亲的负担。育儿过程中(其实家务也一样)的认知劳动基本都是女性在承担。
听到最后的结论就是,真的不要轻易生孩子……
早死早超生,阿焖!
QT: [https://m.cmx.im/@RFYT6PrisonBreak/108628937331902093]
自勉🙏今天就没忍住怼完拉黑了一个来教育我耽美厌女的豆瓣姐……
QT: [https://m.cmx.im/@alic/108629153460985387]
很贊同「寬容原則」
https://alive.bar/@GeXu/108620839240045953
在理解他人說話內容時,要以最大的善意和寬容去理解其用意。這很重要,尤其對於基本觀點一致,已經知根知底的朋友更是如此。別人發表不太完整的陳述(觀點、想法、事實等)時,我們的態度應該是:給這條陳述以最說得通的詮釋,和最善意的初始假設,哪怕這個人在與你爭論。要避免無意義的咬文嚼字和過度解讀。
很贊同「寬容原則」
https://alive.bar/@GeXu/108620839240045953
在理解他人說話內容時,要以最大的善意和寬容去理解其用意。這很重要,尤其對於基本觀點一致,已經知根知底的朋友更是如此。別人發表不太完整的陳述(觀點、想法、事實等)時,我們的態度應該是:給這條陳述以最說得通的詮釋,和最善意的初始假設,哪怕這個人在與你爭論。要避免無意義的咬文嚼字和過度解讀。
#通勤干点啥 周五+周一
时差#13 听完才发现是去年的…人文地理学+人类学+两位主持人,聊城市化、城市空间和人与城市的关系。关于城市化的论述没有给我太惊喜的洞见,对于城市化理论本身知识生产的抽象化vs具体理论中第三世界学者的边缘化还是挺有普遍性的。赵益民谈到的城市的理想状态是“人与人相遇的空间”而非发展主义的逻辑也比较有趣。
东亚观察局 安倍晋三遇袭之后 听得没有太仔细…大概了解了日本政坛的情况,后续关于杀手的背景挖掘会成为各方的烫手山芋(宗教、左右翼博弈乃至外交关系)cue了一下日本愤怒的中年男群体会对政治造成的影响;政治极化的趋势。
由于手机电量告罄还翻了翻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对我而言判断一本书喜不喜欢/好不好的重要标准是看完了会不会很有模仿的冲动……这本书就是这样。城市凝聚着欲望、记忆、视觉、语言。看不见的城市与可见城市互为组成部分。
@Dorothy rwkk
@walunding 壮受嬷可怕如斯
恨安倍晋三的人,因为他参拜过靖国神社和祖辈参与侵华战争就咬牙切齿。按这些人的逻辑,安倍需要尊重战争受害者们,否则就是该死。——那么他们会平等地恨毛泽东与邓小平么?长春围城生生饿死的几十万人,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中死掉的几十万人,天安门广场的冤魂,他们亲手造成的这些血债,不比战犯的后代更值得咬牙切齿地恨?更别说那些为虎作伥者,那些搜刮民脂民膏的红色贵族。仇恨的逻辑多么荒谬。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1984》的结局其实是开放的。
完整地看完了《1984》的人,很少有不为书中描绘的那个暗无天日、没有希望的极权社会感到压抑、沮丧乃至抑郁的。让人沮丧的不仅仅是“大洋国”本身的黑暗,更是面对这样一种极权体制的无力感,仿佛以后的人类世世代代都要接受它的奴役一样。
如果单看正文,不看附录的话,那么读者会有这样的感受是很正常的。即便是看了中文版附录,读者也不会感觉有什么异常。可是当你查看英文原著的附录时,你就会发现这里实际上埋了一条暗线。
我们来将中英两板的附录做一下对比。
中文版附录:
新话的原则
「新话是大洋国的正式语言,其设计是为了满足英社——即英格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需要。到了一九八四年还没有一个人能用新话作为唯一交流手段,不论是口头上的,还是书面的。《泰晤士报》上的社论是用新话写的,但是这是一种特殊的技巧,只有专家才能做到。估计到了二〇五〇年新话终将取代老话(即我们所称的标准英语)。在此之前,它逐步地扩大地盘,所有党员在日常谈话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新话的词汇和语法结构。一九八四年使用的那一种,见诸第九版和第十版的新话词典,是临时性的,其中有不少多余的词和过时的结构,以后就要废除的。这里所涉只是第十一版词典中应用的最后修订稿。
新话的目的不仅是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的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再存在。这样在大家采用了新话,忘掉了老话以后,异端的思想,也就是违背英社原则的思想,就根本无法思想,只要思想是依靠字句来进行的。
……
……
的确,过去的许多文学都已用这个办法加以改写。出于名声的考虑,有必要保持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记忆,同时使他们的成就与英社哲学一致。因此像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拜伦、狄更斯这样的作家的作品都在翻译中;这项工作完成后,他们的原作以及所有残存的过去的文学作品都将统统销毁。这项翻译工作既费时又费力,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二十年恐怕不会完成。还有大量的实用文献——不可缺少的技术手册之类——也需这样处理。主要是为了有时间进行这项翻译工作,新话的最后采用日期才定在二〇五〇年这么迟的一个年份。亅
英文版附录:
The Principles of Newspeak
「Newspeak was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Oceania and had been devised to meet the ideological needs of Ingsoc, or English Socialism. In the year 1984 there was not as yet anyone who used Newspeak as his sol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either in speech or writing. The leading articles in ‘The Times’ were written in it, but this was a TOUR DE FORCE which could only be carried out by a specialist. It was expected that Newspeak would have finally superseded Oldspeak (or Standard English, as we should call it) by about the year 2050. Meanwhile it gained ground steadily, all Party members tending to use Newspeak words and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more and more in their everyday speech. The version in use in 1984, and embodied in the Ninth and Tenth Editions of the Newspeak Dictionary, was a provisional one, and contained many superfluous words and archaic formations which were due to be suppressed later. It is with the final, perfected version, as embodied in the Eleventh Edition of the Dictionary, that we are concerned here.
The purpose of Newspeak was not only to provide a medium of expression for the world-view and mental habits proper to the devotees of Ingsoc, but to make all other modes of thought impossible. It was intended that when Newspeak had been adopted once and for all and Oldspeak forgotten, a heretical thought—that is, a thought diverging from the principles of Ingsoc—should be literally unthinkable, at least so far as thought is dependent on words.
……
……
A good deal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past was, indeed, already being transformed in this way. Considerations of prestige made it desirable to preserve the memory of certain historical figure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bringing their achievements into line with the philosophy of Ingsoc. Various writers, such as Shakespeare, Milton, Swift, Byron, Dickens, and some others were therefore in process of translation: when the task had been completed, their original writings, with all else that survived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past, would be destroyed. These translations were a slow and difficult business, and it was not expected that they would be finished before the first or second decad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re were also large quantities of merely utilitarian literature—indispensable technical manuals, and the like—that had to be treated in the same way. It was chiefly in order to allow time for the preliminary work of translation that the final adoption of Newspeak had been fixed for so late a date as 2050.」
看出区别来了吗?
区别就是中文版附录是用现在时写成的,英文版的附录则是用过去时写成的。时态不一样,意思就天差地别。中文版的附录实在描述一个正在推行的制度,英文版的附录则是在描述一个曾被推行的制度。我查看了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三家的译文,发现它们都没有把译文中过去时时态表现出来,它们都遗漏了这处重要的信息。
知道了原著的附录采用的是用过去式的视角,我们就能够明白附录中的“新话”和“大洋国”其实是后人记录或研究的对象。这里暗示的是“大洋国”可能最后还是被推翻了,人们也许把曾经在大洋国发生的这些事情总结成了历史教训,用以警示后人。当然,这是一种猜测,因为奥威尔透露的信息实在太少,没有人知道附录的作者是谁,没有人知道两者之间隔了多少年,也没有人知道这么多年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从《1984》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其实能够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例如《1984》中反复地提到过一句话:“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一定在无产者身上”。这是温斯顿在日记本里记录的内容,在文中出现过三次。具体的解释是这样的
“因为只有在那里,在这些不受重视的蜂拥成堆的群众中间,在大洋国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中间,摧毁党的力量才能发动起来。党是不可能从内部来推翻的。它的敌人,如果说有敌人的话,是没有办法纠集在一起,或者甚至互相认出来的。即使传说中的兄弟团是存在的——很可能是存在的——也无法想象,它的团员能够超过三三两两的人数聚在一起。造反不过是眼光中的一个神色,声音中的一个变化;最多,偶尔一声细语而已。但是无产者则不然,只要能够有办法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不需要进行暗中活动了。他们只需要起来挣扎一下,就像一匹马颤动一下身子把苍蝇赶跑。他们只要愿意,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党打得粉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迟早会想到要这么做的。”
此外,在奥威尔的其他文章中,也能看到类似的观点,例如在《动物农场》乌克兰文版序中,奥威尔就回忆到他曾经看到过一个小男孩,大概十岁,赶着一匹拉车的大马在一条狭窄的小道上走,那匹马一想转弯,那男孩就用鞭子抽它,见此场景,奥威尔就想到,如果这些牲口知道它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就无法控制它们,人类剥削牲口就像富人剥削无产阶级一样。
在评论伯恩汉姆的那篇“Second Thoughts On James Burnham“里,其实也有类似的表示。其实说到底,奥威尔一直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像他这样的社会主义者,特点就是不论现实让他多么灰心沮丧,都依然会保留对普罗大众的信心,也许极权统治能维持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但它总会有被推翻的一天,人类从来都没有建成社会主义,不代表以后就不会建成。这里的社会主义,是指奥威尔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
总之,《1984》的结局是开放的,极权主义很可能最终还是被推翻了,如果你知道了结尾用的是过去时再去看这本小说,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
关于今日大新闻:
“这福气给你要不要啊?”
“我要!!!”
@cat 好怪,再看一眼
#通勤干点啥
早上听了喜欢的po主推荐的中间地带最新一期播客,关于近现代中国与东南亚、中印交流以及西方角色的历史嬗变。由下至上的视角非常新颖有趣,也相当程度刷新了我之前对中印交流史的基本认知。印象比较深刻的点:郑和下西洋主要是政治行为,在民间经济文化交流上的意义并不大;鸦片战争前,鸦片主要经由印度输入中国;二战时期在印度的中国人才爆发式增长,中国有十几万军队、飞行员都是在印度加尔各答等地训练的,印度是名副其实的抗日“大后方”;象征中美关系的“飞虎队”中的队员很多是走私犯,与中国商人合作走私手表、钢笔、电池,蒋介石因不满走私犯伤害国民政府国际形象处决了两名商人;广东人在印度做皮革生意卖皮鞋,湖北人做牙医,山东人卖丝绸。
晚上听了不合时宜最新期,詹青云与林垚就罗诉韦德案被推翻的对谈,两位法律人比较清晰地勾勒出了罗诉韦德案的历史逻辑与制度实践、保守派与自由派的争执、堕胎本身涉及的法理与道德观、对美国民主未来的悲观预期。对谈很丰富,可以延伸的东西太多,甚至提到最高法院终身制是对维护少数人权利不受多数人决定的民主预期。比较超出意料的是林垚提到保守派“反堕胎”的论题本身是被建构出来的。罗诉韦德案的判决是由共和党法官作出来的,当时共和党中多数是支持堕胎的。但共和党为争取宗教保守派选票,有意使用了“堕胎”议题并进行意识形态宣传,而这形成了对自由派强有力的反攻。之前以为的意识形态问题,其实是政治与历史问题。
@Dorothy 代餐罢了!
- 比较无知的
- 女权主义者
- 每天要喝一杯
- 咖啡
- 性癖是
- GBG/弱攻/美攻/虐攻/受苏
语词通过灌输一种思维方式进而催生一种符号暴力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