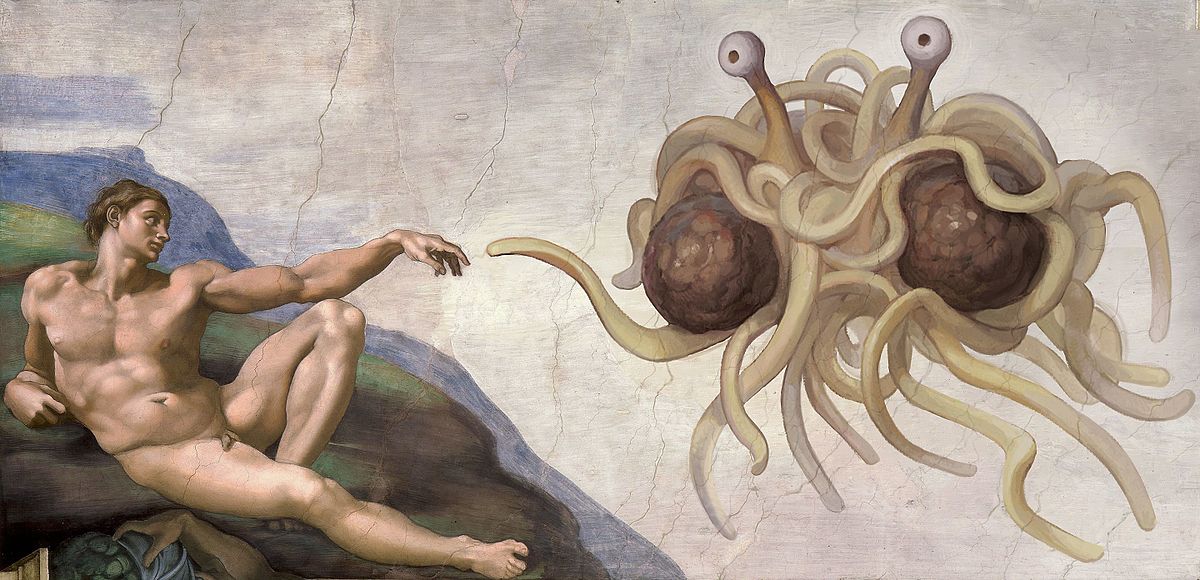@OliviaVitti (一个同好举手)小时候边被吓边忍不住看233~至今仍记得埋在森林的白骨和记忆宫殿——
@Hitchhiker 嗷好哒!谢谢小猫ww
@seanmiona 我没收过点星的提醒,有次转嘟因为嘟主编辑了几次而连续收到几次提醒才发现的~Miona可能是关了这个功能?
也许有友邻方便解答:假如嘟主在有人转发后编辑嘟文,转发者会收到「编辑」的提醒通知,那么请问点星也会收到吗?(因为本人有修改嘟文的习惯,如果会有提醒就尽量不改了~以及「编辑」提醒功能可以在通知里关掉)
漫谈(随记的文字还嫌嘈杂,等读毕回思再修缮,这两日读书想到旁及的一些事)
去年读王维集的时候推荐友人读辋川集,特意嘱咐她别当成CP游记(省略背景),否则大抵会失望。由此想到人们出于某原因读某部书,也许会因为没寻到想要的(接触前的误判),又忽视书中别的好的部分而完全错过了,没有「与我想象不同,但寻到想象之外的佳处」的愉悦。
然而后来师友问起诗读得如何,我说王维还写了体量庞芜的应制酬和诗,缺乏诗味读得兴味索然。 老师说那些本就不是有真交情的文人的往来闲赋,很可能只是王维以文名盛,有些官员调职前有意留诗作纪念,王维收到暗示后写来打发,对这些诗看文采就够了,不必追求太多。
是啊,这让我惊异于同一事理置于不同场景就忘了,还会在别的时候反复忘记。
最近读波德莱尔想起这桩事。从思想性看,我自然拒绝理解他视所有女人(年迈故去的女仆除外,见《满腔热忱的女仆》)为(潜在)情欲对象并感到厌烦,除反复加深选材颓废荒糜的观感外一无所获。而这只是初阶的认知。现在继续读我不得不考虑他是将生命的荒芜(他所认为的生命本质)与欲望宣泄同构,又和一般并举性与死的体验写作有何不同。
事实是,只要继续读,我就会不断地从男性作家笔下感到不同程度的生理不适。中国文人再避讳也有《玉台新咏》这样物化处理的诗,外国文人则数不胜数。
然而倘若因此采取拒绝姿态只能暴露我的业余。思想不合便察看情感,都不合便看技巧,一名成熟作家不会毫无技巧。像帕乌斯对评论家的回应「你们不能纠结于我没写的部分,而应该看我写了什么」,同理,我不能要求作家给出他没有的东西,得看他有什么,这依旧是上述的理由。即便第一次读被个人主观好恶带偏,再读便必须抽离地欣赏,否则还做什么研究。
@seanmiona 据我观察,人读纸质学术书似乎有长期阅读纸书导致没法用电子设备做深度阅读的原因,尤见于读哲学一类晦涩的书(个人是这样)。不知Miona是否尝试过读纸书同步拍照,用图片转文字软件之类方法转存(虽然也蛮麻烦的,谁让找不到电子版……
#book/泰戈尔诗选_园丁集 35
「你的要求比别人的都多,因此你才静默。
你用嬉笑的无心来回避我的赠与。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妙计,
你从来不肯接受你想接受的东西。」
冰心/译
《雪国》
#book/雪国
没译本可挑,川端康成在市图远不如夏目漱石有排面。
读这本的时候似乎能试着根据翻译的文意想象而非细究文字,比如「她的眼睛同灯光重叠的那一瞬间,就像在夕阳的余晖里飞舞的夜光虫,妖艳而美丽」,能想象画面是美的。
不仅是结构松散,对话也前后不搭,像剧本里双方各怀心思的交错对话。场景变换、时间流转像忽然发生的,仿佛不经加工地呈现收集好的各式素材。乍看几近无情节可言,仿佛中间略过十页也不妨害理解,然而内在递进不可更替。
三年时间线里驹子的恋情像在降生之初就冰冻在同样的温度,而岛村的反应也如冰冻般无动于衷,不知是原文含蓄还是译文有误,两人已亲近至狎昵状却又似不曾发生过任何,一直幽会而情感状态毫无变化,仅仅是一对寂寞人暂时作伴。
「岛村猜想驹子准是误会了,不由得大吃一惊,他闭上眼睛,一声不响」像这样认为对方误解了也不解释,驹子则「算了,你会忘了的」。
驹子和叶子都情感炽烈,然而照进现实却像立即被雪国的冰冷和他人的孱弱压制熄灭了似的,所以岛村离开前的火灾是一次疯狂感情的集中释放,只有这一刻连岛村也震撼如银河坍塌。
川端康成自己说小说是随写随载的,没有特意规划,然而小说从岛村第二次去旅行写起,时间上先认识驹子而行文上叶子更早出场,最后火灾的重心也在叶子而非驹子,叶子外在于作者地成为了线索,具体作用则影射岛村对驹子的感情,如她的投影重叠着山峦,岛村对驹子也是外于接触的欣赏,只要主观构建的投影而非实体。
「她呆呆地望着岛村,忽然带着激昂的语调说:“你就是这点不好,你就是这点不好!”
驹子焦急地站起来,冷不防地搂住岛村的脖子,她简直方寸已乱,顺嘴说了一句:“你不该说这种话呀。起来,叫你起来嘛。”说着她自己却躺了下来,狂热得不能自已。
过了片刻,她睁开了温柔而湿润的眼睛。“真的,你明天就回去吧。”她平静地说过之后,捡起掉落的发丝。」
风物描写则自然融入情境,凭意识流动转变,不是绘画式而是电影式的摹景。
「货车通过之后,就像摘下了遮眼布,可以清楚地看到铁路那边的荞麦花挂满红色的茎」
「黄昏的景色在镜后移动着。也就是说,镜面映现的虚像与镜后的实物在晃动,好像电影里的叠影一样。出场人物和背景没有任何联系。而且人物是一种透明的幻象,景物则是在夜霭中的朦胧暗流,两者消融在一起,描绘出一个超脱人世的象征世界。特别是当山野里的灯火映照在姑娘的脸上时,那种无法形容的美,使岛村的心都几乎为之颤动。
在遥远的山巅上空,还淡淡地残留着晚霞的余晖。透过车窗玻璃看见的景物轮廓,退到远方,却没有消逝,但已经黯然失色。尽管火车继续往前奔驰,在他看来,山野那平凡的姿态显得更加平凡。由于什么东西都不十分惹他注目,他内心反而好像隐隐地存在着一股巨大的感情激流。这自然是由于镜中浮现出姑娘的脸的缘故。只有身影映在窗玻璃上的部分,遮住了窗外的暮景,然而,景色却在姑娘的轮廓周围不断地移动,使人觉得姑娘的脸也像是透明的。是不是真的透明呢?这是一种错觉。因为从姑娘面影后面不停地掠过的暮景,仿佛是从她脸的前面流过。定睛细看,却又扑朔迷离。
车厢里也不太明亮。窗玻璃上的映像,不像真的镜子那样清晰。没有反光。这使岛村看得入了神,他渐渐地忘却了镜子的存在,只觉得姑娘好像漂浮在流逝的暮景之中。
这当儿,姑娘的脸上闪现着灯光。镜中映像的清晰度并没有减弱窗外的灯火。灯火也没有把映像抹去。灯火就这样从她的脸上闪过,但并没有把她的脸照亮。这是一束从远方投来的寒光,模模糊糊地照亮了她眼睛的周围。她的眼睛同灯光重叠的那一瞬间,就像在夕阳的余晖里飞舞的夜光虫,妖艳而美丽。」
不过经常用一种——与其说句式不如说思维:「认为某物在躲避黑暗的吞噬」的主观映射,比如
「若在夏天,红蜻蜓漫天飘舞,有时停落在人们的帽子上、手上,有时甚至停落在眼镜框上,那股自在劲儿,同受尽虐待的城市蜻蜓,真有天渊之别。
但是,眼前的一群蜻蜓,像被什么东西追逐着,又像急于抢在夜色降临之前不让杉林的幽黑抹去它们的身影。」
「一个十九二十岁的乡村艺伎,理应是不会弹出一手好三弦琴的。她虽只是在宴席上弹弹,可弹得简直跟在舞台上一样!岛村心想,这大概只是自己对山峦的一种感伤罢了。」
现在读到无感的作品也得做摘抄了,选录的是我视为核心而非欣赏的部分,试图给未来的自己留下一点线索。
本号是用来关注友邻的魂器,主号在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