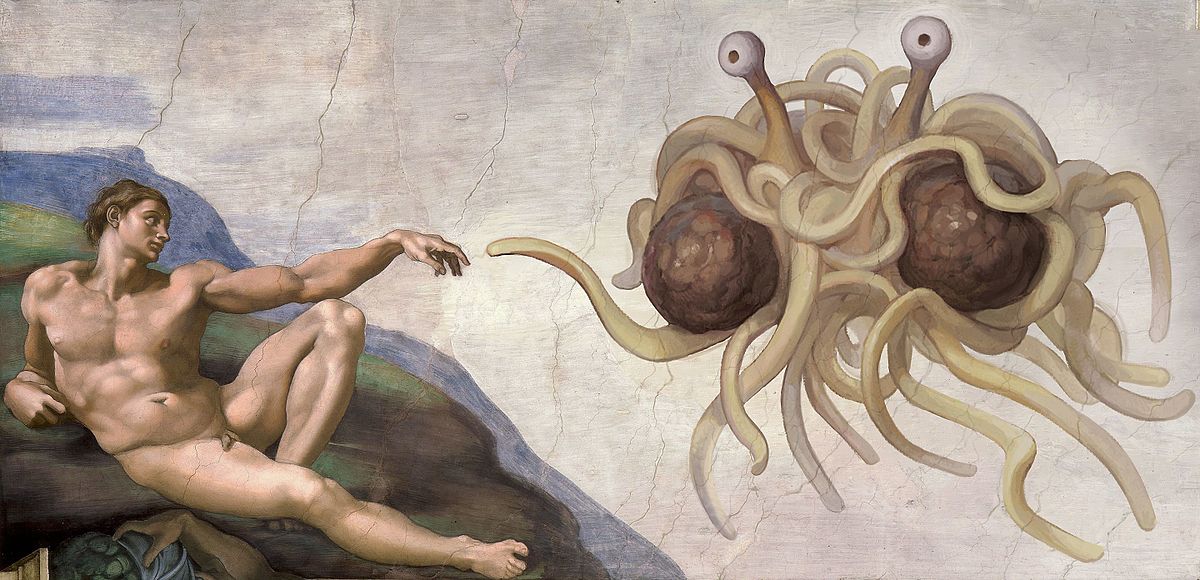好久不看乌克兰的新闻了。今天翻了一下,又被震住了。这个战火中的国家是怎么做到的,也太文明进步了。
战争时期本应该是最民族主义情绪高昂,丛林法则盛行,中央集权一言独大的时候,乌克兰却在推同性婚姻合法化。
第一夫人Olena为乌克兰被家暴的女人做了一款手机app,可以在不被家暴犯觉察的情况下一键报警。
我又想起之前布查大屠杀之后,那里的人民请求总统说能不能帮忙照顾流落街头的小动物们,为它们也提供食物。
还有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老奶奶给俄罗斯士兵塞向日葵的种子。“等你死了,向日葵会开花。”这是诅咒吗?我更愿意当这是一种祝福。如果那位俄罗斯大兵脑子清醒一些早点放下屠刀的话,再过几年成为欧盟成员国公民也有可能。
怎么会有这么文明的地方。怎么会有这么了不起的人民。怎么会有人可以在战火和侵略和屠杀后还说,战争的胜利不值得庆祝。
荣耀属于乌克兰。
新闻来源:
1. 同性婚姻: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2/08/04/ukraine-zelensky-gay-marriage/
2. 反家暴app:
https://odessa-journal.com/the-ministry-of-internal-affairs-and-unfpa-with-the-support-of-the-first-lady-launched-a-mobile-application-for-calling-the-police-in-cases-of-domestic-violence/
#通勤干点啥
几天都在地铁上看了微信读书上的《绝叫》by叶真中显。
不知道日本读者读着会是怎样的感受,同为东亚人,为其中表现出日本社会的特征之熟悉感到十分惊诧(重男轻女、民粹主义年轻男性、派遣劳务、泡沫经济、游民问题…)果然东亚文化现代化有内在相似之处。是非常精彩的社会派推理,双线叙事的结构和节奏都恰到好处。为阳子的强韧生命力惊叹。书封推荐语所谓“恶女编年史”完全不对啊!阳子哪里是恶女,除了最后为了摆脱泥淖的breaking bad以外,她做的一切都只是不想屈服于命运。甚至可以说,阳子的悲剧是日本战后现代社会发展悲剧的缩影。
好看是很好看,不过住着真的舒服吗 ![]()
QT: [https://acg.mn/@yourshot/108752066684468506]
#通勤干点啥#
螺丝在拧紧41 与独立记者柏琳对谈。柏琳是我会非常佩服的一种人,行动力强、心态开放豁达,如她自称的是性格很“柔韧”的人。不会被外部困难打倒而是越挫越勇,things did not kill her made her stronger.内在世界极其坚硬完整。适合打工人上班前打鸡血用(?)
《克莱因壶》 前面几章有点性别角度的槽点不过整体值得一看。一个半小时翻完,阅读快感强,同样适合通勤(只要别入迷到坐过站)。80年代末的作品有这样超前的脑洞着实厉害,虽然这几年元宇宙概念太火导致小说的核心诡计不那么使人眼前一亮(感受到带科幻元素的类型小说还是挺有时效性的)。但叙事技巧和结构实在精巧,让人禁不住一口气读完。
作为一个不想结婚建立家庭,也不想有后代的异性恋,我在思考自己的死亡时刻时,也的确会感到茫然。
传统模式下大部分人都默认自己在重病和临终时会有伴侣和孩子陪伴。而对于我和一些不想结婚的人,也往往会因此面对“那么你老了(直说就是“快死了”)时怎么办”这种问题。
不必拿很多人即使已婚有后代,依然孤独地应对重病和死亡的现实来反驳这个问题,那是斗嘴而已。我们得承认这并不是在小题大做。它的确是棘手的,必须思考并提出解决方案。
这也是我看到同性群体如何一同照顾患重病(书中以艾滋病患者为主)的朋友离开人世时,会那么感动感慨的原因。
重新寻找和建立自己的“家人”——即使里面的成员间没有血缘或性的关系,承诺对彼此的爱和责任,并像传统的家人那样陪伴对方到最后时刻——只是想想就好让人感动,也好想像已经这样做了很久的同性群体学习。
如果不想走入传统的婚姻,那么有没有可能和一个或几个真诚的朋友成为彼此家人般的存在呢?同性群体明明已经证明了这是可能的了,我好惊讶自己以前却不敢确信。也许我们作为异性恋的确视野狭窄,太执着于异性恋的家庭模式,包括执着于逃离,都看不到同性群体里也会有没有性关系和血缘的“亲人”角色。
今天还很巧地在读巴黎评论对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访谈时,也看到了一段她解释自己和格雷丝·弗里克(往往被认为是她的同性伴侣)间关系的话:
“什么是爱?是这种热情、这种温暖,推动着一个人坚定地走向另一个人。为什么要把人的生殖系统看得那么重要?这无法定义一个作为整体的人,即便从情欲层面来说,也不是这样的。就像我说的,重要的是情感、关系。但是,你会爱上谁,取决于各种偶然性。”
我们会爱某个人,并不是受生殖系统决定的,情欲可能在某些时候有影响,但影响的因素太多了,“爱”当然不等于“欲”。即使是“欲”,也不仅仅有生理层面的,还有情绪的、智识的。我们会爱谁,也绝非因为遇到了一个异性或同性,而是机缘巧合遇到了某一个“人”。
异性夫妻家庭模式会成为传统,其实也是因为传统生产模式造成的,可是过去半个世纪里生产模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到了可以进行新模式实践的时候了呢?
我能想到的离开时的状态,除了希望尽量平静、有尊严,也希望即使在无法足够平静有尊严时(毕竟舍温·努兰说了后一种才更常见),至少能有那么一个或者几个视彼此如亲人的好朋友在身边。这真的远远比什么“丈夫”“孩子”在身边更吸引我。死作为一个必然发生的事,影响到的就是那些我爱过和可能爱我的人,而他们绝对不会是通过婚姻或者生育带出现在我生命中的。
所以如果以后再被问到“那么你老了时怎么办”,也许我可以回答说:“我会努力寻找可以待彼此如家人的朋友,和他们建立互相陪伴的关系,所以不会和传统婚姻模式中的那些人有区别。我相信这是可能的,因为多年以前同性群体中就明明有好多人做到了。我只是需要去寻找和实践,像所有人一样。”
#通勤干点啥
螺丝在拧紧vol40
比较轻松的一期播客(第二次听更加确定了,吴琦的声音是我喜欢的一款知性男声 ![]() ),主播和嘉宾对谈关于观看电视剧的历史和体验。电视剧,一类电视诞生之日起就在被批判的大众文化,如今成为一份现代生活的“解药”。刚好今天追完BCS的更新,对于播客里谈到的电视剧的“陪伴”作用和由于长周期而赋予个人的独特记忆恰有所感。嘉宾认为目前观众对“药”的要求是“疗效”,以此来解释为何现在的电视剧市场细分、观众对电视剧的剧情要求“苛刻”了起来(比如不喜欢be)。而同时社交媒体与平台的发达,也使得创作者和观众之间不再有任何格挡。此处还cue了一下前段时间晋江作者自杀的事件。由此我倒是联想到一直以来没想清楚的问题:现在的创作在多大程度上是属于作者的创作?尤其是网络文学,它很多时候在学术研究中并不作为文学而是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娱乐产业被看待。作品、平台、作者、读者好像是浑然一体的娱乐产物。甚至此时还碰瓷不到罗兰巴特“作者之死”的环节,而是面向读者的表达本身已经处于非个人的互动当中。所以某种程度上,也总觉得网文的确是一种售卖的“商品”。
),主播和嘉宾对谈关于观看电视剧的历史和体验。电视剧,一类电视诞生之日起就在被批判的大众文化,如今成为一份现代生活的“解药”。刚好今天追完BCS的更新,对于播客里谈到的电视剧的“陪伴”作用和由于长周期而赋予个人的独特记忆恰有所感。嘉宾认为目前观众对“药”的要求是“疗效”,以此来解释为何现在的电视剧市场细分、观众对电视剧的剧情要求“苛刻”了起来(比如不喜欢be)。而同时社交媒体与平台的发达,也使得创作者和观众之间不再有任何格挡。此处还cue了一下前段时间晋江作者自杀的事件。由此我倒是联想到一直以来没想清楚的问题:现在的创作在多大程度上是属于作者的创作?尤其是网络文学,它很多时候在学术研究中并不作为文学而是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娱乐产业被看待。作品、平台、作者、读者好像是浑然一体的娱乐产物。甚至此时还碰瓷不到罗兰巴特“作者之死”的环节,而是面向读者的表达本身已经处于非个人的互动当中。所以某种程度上,也总觉得网文的确是一种售卖的“商品”。
- 比较无知的
- 女权主义者
- 每天要喝一杯
- 咖啡
- 性癖是
- GBG/弱攻/美攻/虐攻/受苏
语词通过灌输一种思维方式进而催生一种符号暴力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