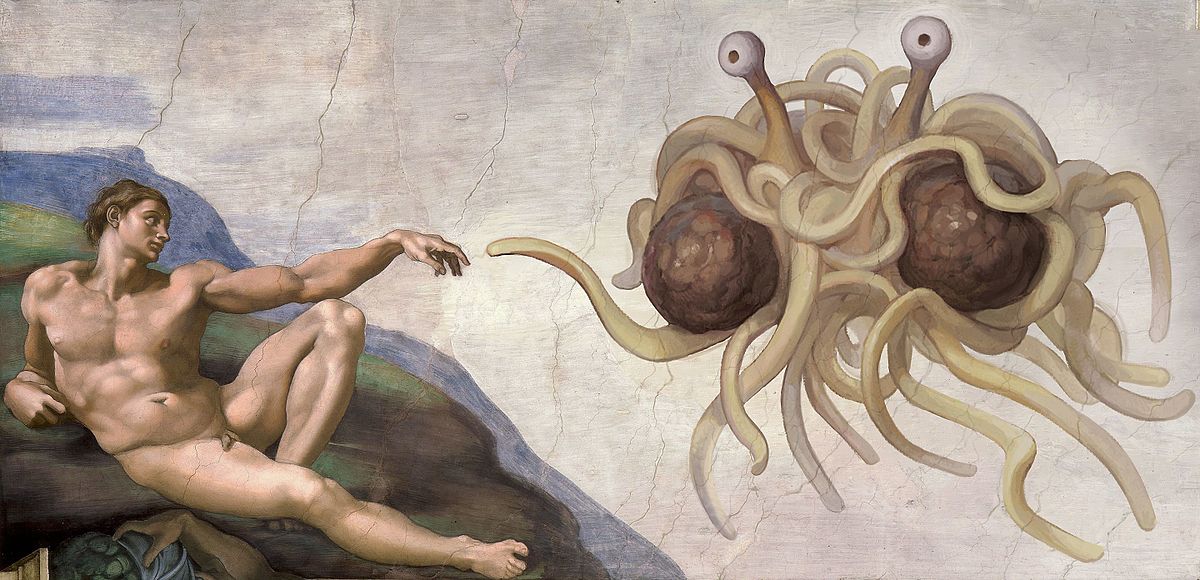看前面的部分:哀悼被疫情耽误的毕业旅行;看后面的部分:哀悼北京被清退的“低端人口”。
QT: [https://pullopen.xyz/@guanzhi/108474787654891803]
『在铁路上开餐』
作者:梁文道
在日本坐火车旅行,其中一个乐趣是可以吃到美味的铁路便当。别小看这些并非现做因而盛放在保温器皿里的食物,它们可都经过精心配制,虽经水汽持续蒸腾,但风味别具。而且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例如“明石便当”,一个小陶瓮里装着炖煮得软熟耐嚼的章鱼饭,光是外形就已经可爱了。讲究点的,还可以在各个车站百货公司里搜寻名店豪华出品,带进车厢格外炫目。
一边看着窗外景色朝身后飞逝,一边慢慢品尝不止充饥而且适口的食物,这是在香港久违了的滋味。没错,在九广铁路香港段仍未被“港铁”吞并,在列车仍未完全电气化的年代,我们也是可以在火车上吃东西的。甚至到了电气化时代,我还记得有些村妇背着竹篓,一节节车厢叫卖可能是自家种的落花生。我又记得,最是怀念“旧时香港”,同时也最反对内地“蝗虫”的陈云,好像也记过一笔这难忘的风景。是谁消灭了这良佳淳厚的庶民风俗?我想大概不是所谓的自由行“蝗虫”吧。二十多年来,香港的地铁和火车愈来愈干净,人人循规蹈矩、面容冷肃;但我依然见过不少人在车厢里公然饮食。都不是内地来的游客,却往往是一些膝上陈放着公文包的白领,他们姿态佝偻,十分疲惫,匆匆忙忙啃食一块用塑料袋包好的面包。如果是早上,我能想象他根本来不及吃早餐,急着出门以免误了上班的时间;如果是傍晚,我能感到他耗尽了精力,在叹一口气的间缝里疗养肠胃。
我们不让这些人在车厢里饮食,不让放学的孩子在车中零嘴,甚至一些病人喝水都要特别解释,为的是什么?据说是为了干净。说到干净,世上恐怕还真没有比香港更干净的铁路了,干净到车站里头没有厕所的地步。就和小贩绝迹香港街头一样,听说也是要使市容更加整洁。每次在香港辩论小贩政策,我都会想起日本,因为日本的街上也有小贩,甚至面摊;但他们的环境难道要比香港脏乱吗?同样的,日本的火车也不见得比我们的港铁更污秽吧?
不建厕所,不准饮食;说穿了,这不是卫生考虑,而是节省管理和清洁的成本,更是肆虐香港达数十年之久的“管理主义”幽魂。请注意,它不一定更善于管理,只是更能斩草除根地净化一切而已,把整个铁路系统净化成一个不能吃喝拉撒的纯粹交通空间,犹如将街道净化成一个无法停留闲散的单纯通路一样。讽刺的是,在赶走了在车厢里卖花生和钵仔糕的阿婆,以及九龙塘车站内那间卤水味飘香的小吃店以后,他们却加进了永不休止的电子屏幕,把乘客全数卖给广告商。东京的电车准许饮食,纽约的地铁也准许饮食,香港不行。不止不行,我们这些被商家和“管理主义”绑架了的香港人,还要把这套禁令上升到文明的象征,捍卫铁路公司的利益变成了捍卫香港人的身份尊严。
我对一些语言革命的走向也不看好。诚然,确实有许多被污名化的概念,它们当然有被澄清甚至修改的必要,但有些人试图呼吁的修改在我看来实在有些荒诞——最不可理喻在于,一些人竟然试图仅靠语言表象来判定人心,甚至花大把时间在约束他人身上,堪比文字狱,简直是本末倒置,根本搞不清重点!世上不知有多少表达粗糙却一心向善的人,也不知有多少文质彬彬道貌岸然之辈,你们确定要靠这样来提纯盟友、决定敌人吗?
我甚至还遇到有人这样斥责她人:“你不能在说‘他妈的’这个词的同时自称女权主义者”。完全无视对方在表达的内容本身有多重要,无视人的情绪,无视人的习惯,无视语言发展本身的规律……真是太让人无语了。
最近能让我大喊一声“嗑到了”的cp是《风骚律师》里面的Kim与Jimmy:努力专业一本正经但也灵活变通偶尔越轨使坏的女主&擅长骗人说谎小偷小摸试图改邪归正但屡屡受挫的男主
这个视角有意思,温柔是对对方主体性的绝对尊重,让事实归于事实
QT: [https://alive.bar/@normanzxy/108469611665107589]
强大和温柔是一体的。因为只有在“无我”的状态下,才能完完全全只考虑对方的感受。而前者是强大的极致,后者是温柔的本义。
我读到过的最温柔的一个小故事,是说一个父亲,让女儿把满屋子的玩具,分享一点给来访的小朋友玩。女儿不肯,哭闹起来。这个父亲的反应是:“可怜的孩子,生命中从来没有过真正拥有某个东西的体验,所以也就不知道什么是分享的乐趣。”
当时看到这里惊呆了,心说父母遇到这种事情的第一反应,难道不是孩子冷漠自私不听话吗?可是仔细一想,非常有道理——分享当然是快乐的,但前提是要“拥有”。孩子虽然有一屋子玩具,但是从来没有过“由自己决定是不是给别人玩,给了之后,别人还能还给自己”这个完整的过程,所以她只是表面上“有一屋子玩具”,却从来没有过对于“所有权”的感觉。既然没有过真正的“拥有”,你又跟她谈什么“分享”呢?
而且更妙的是,这并不是一个育儿故事,只是作者在讲别的事情时顺便提了一句,也没有进一步展开分析,似乎觉得是个天经地义的反应。我之所以说这是“最”温柔的一个故事,关键就是最后这一点。
而进一步分析你会发现,这个父亲之所以能够这么温柔,关键是因为,他看到的只是事实的原貌,也就是“孩子不愿意分享”,而不是添油加醋的“孩子不听话/不给我面子”。前一个是“无我”的视角,后一个是“有我”的视角;前一个是“处于害怕自己的威权受到挑战”的应激状态,后一个是“孩子无论怎样反应都不是冲着我来的”松驰和客观中立的状态。
唯有强大,才能松弛;唯有松弛,才能理解;唯有理解,才能温柔。
一下子能对号入座很多简种特色平权人和反跨粉红女权…
QT: [https://m.cmx.im/@yun5/108468610359348424]
我向来同意女性女权主义者对“女权男”的所有指责。在简中环境下绝大多数男性都在娃娃学步阶段,自称女权男的人群里总是帮倒忙和有私心的居多,这个群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被扫射是必要且正当的。
但其实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高危群体,那就是男权女。
她们往往携带着大部分父权社会构成的文化习性,即强者对弱者的剥削。表现形式为“我是老师,所以我更会教人”、“我人生经验比你丰富,所以你该听我的”、“你都意识不到你自己的问题,让我来告诉你”、“你这样的做事方式不正确,要像我这样做才对”、“我教你做人是因为我关心你呀”等等爹味发言。
在女权议题上,她们总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立场。她们看到比较愤怒激进、勇于表达自己、挑战强者的那些女性,就会跳出来说“那样太激进了,我不喜欢”。看到鲜有男性发表言论的时候会说“我觉得也很需要你们男性的观点,我们不应该割席”。但当有男性试图讨论女性议题时,她们又会说“你们这些观点我早就说过了”、“你们不是女人所以你们不懂”。如此反复横跳,强调自己高人一等,充满着父权主义特色,说着看似永远不会错的废话。
这种人的危险就在于会成为任何运动中的搅屎棍。一方面她们通常没有任何女权主义理论,都是从个体经验出发,在看到弱者受伤时说“我和我周围的女性朋友都不会这样啊”,看到弱者反击时说“你们这样激进只会让男人对我们更反感”。
这样一来就会让整个父权社会看到:噢,女人也有不觉得这个问题多严重的,那女权问题果然是个别激进女权搞的东西。
她们相当于埋伏在女性群体中的卧底,如果男人都是狼人,这些男权女就是被丘比特连在狼人身上的乱民。她们真正在意的只有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形象、自己要获得最终的胜利。为此不惜牺牲掉活跃派女权以及那些试图帮女权发声的男性。
她们借助女性身份和七拼八凑的女权理论在女权阵营里左右横跳,又抱着固有的父权保守思维阻碍运动和变革、打压反对她们的女性男性。她们试图在任何场合中都占领权力制高点:“我最懂”、“我最成熟”、“我最关心你们”,因为在她们的父权社会观念中:高位者才能不被剥削。
这种人需警惕。
#一些键政
“丧事喜办”可以说是真理部的看家本领了。它的“吸纳性”与“排他性”在面对任何群体性事件、天灾人祸的时候都自洽到无懈可击。万柳令人激动的拆墙事件后,是学工部、团委、餐饮中心对这一长久被忽视的校外住处的“关怀备至”和宣传推送,也是万柳原本高度独立的学生组织遭遇收编危机,还是辅导员直接进驻楼层,以层为单位的细化管理。
唐山事件上为什么一定要反对国家现在力推的“打黑除恶”视角对于性别视角的抹除和解构,因为如果此事被归入国家“打黑除恶”的宏大叙事中去,中国女性不管在公共场合和家庭领域都容易遭受性别暴力的处境,都将不会获得任何改善,当此事掀起的舆论被针对男权社会“无害化”后,对于唐山罪犯的激烈抨击将不会阻止下一个女性在北京,上海,西安,沈阳,广州的任何一个街头和家里遭受暴力攻击无人援手的场面,因为只有被官方盖章认证为“黑社会”的施暴者,才会在事后(只有在事后),并且只允许由国家出面,依据施暴者扰乱现有秩序的程度(不是依据他对于妇女的侵害程度),进行处理
如果任凭“打黑除恶”的宏大叙事收编唐山凶案,那么此事过后获得强化的只有国家机器,妇女对于男性同盟性别暴力的反抗会再一次被狡猾地消解和利用,被利用来伸张国家的威严,被利用来进一步巩固新冠期间已经发展得非常明显的公权力对民间的监控
- 比较无知的
- 女权主义者
- 每天要喝一杯
- 咖啡
- 性癖是
- GBG/弱攻/美攻/虐攻/受苏
语词通过灌输一种思维方式进而催生一种符号暴力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