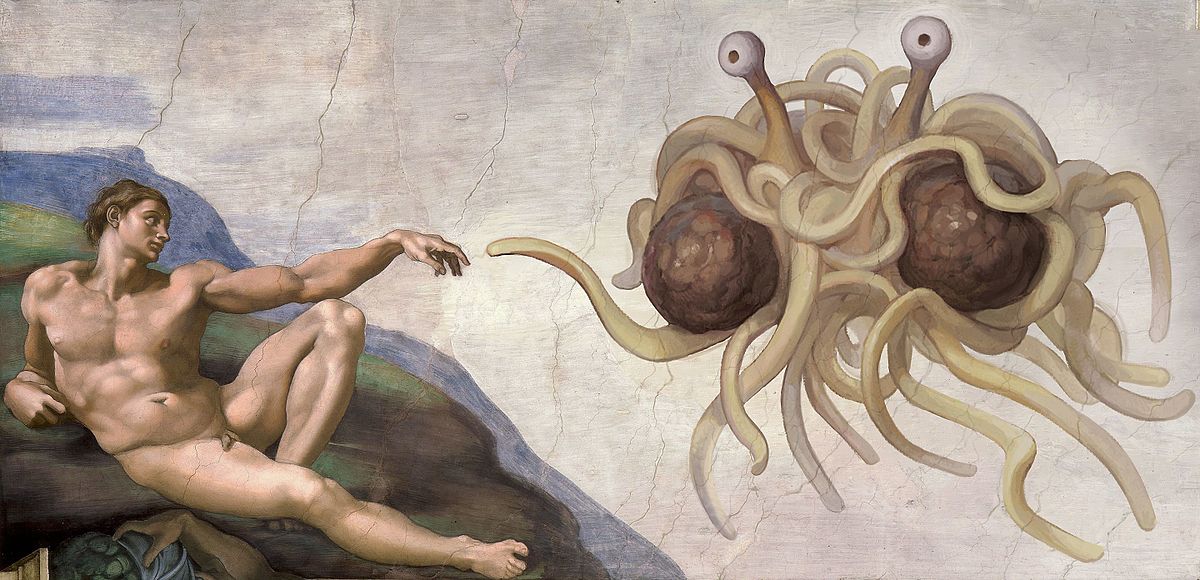又回想起来疫情期间集体注射疫苗的事情。
我们本地的室内公共场所是体育馆,那时还是冬天,全校师生集体来排队。我讨厌死了口罩的触感,根本不管父母的叮咛,总是偷偷把它揪到鼻尖下面,就这样,呼吸处还总是连接着一片湿而冷的水汽。
激光打完注射卡,捞起左臂的袖子(那时我还在高考,右手要留来写字),医护人员掰开疫苗小管有清脆的咔嚓声。我其实怵头,回想起小时候父亲说不看就不痛了,少年脾气上来,便逼着自己直视,脑袋僵直得像颗强扭的瓜。很多人都说打新冠和狂犬疫苗一样,打完痛得使不上力气,但我只有第三次肌肉注射极痛,由于自诩很会忍耐,就风轻云淡地硬撑,还要去主动招呼同学聊天。
注射完要在场等待三十分钟,不大的体育馆中间摆了很多塑料凳子,饮水机有温水,所有到场的人不知为何都在狂喝。那时候,体育馆的木地板经过累月的踩踏带有一种温润的油黄褐色,木块松动,行走中和鞋底磕碰出硬硬的嗒嗒声。踩在那样的地板上,恍惚中觉得好像正在参与一场大型活动——尽管周围围绕的不是帘幕而是白色个隔离屏风,还充斥着消毒水和体育场胶皮的味道。
像是初一时被组织起来的元旦联欢。在中学的大体育馆里,我们摩肩接踵地坐在塑料凳上,巨大的幕布被钢筋吊起,在舞台上放射出深邃的阴影,空气潮热,人们突如其来地为闪亮登场的演员们鼓掌。那样的演出颇有抽离感,我不时被演出的吵闹带跑,又低头翻看自己带来的小说和作业——然后被一首《vois sur ton chemin》的合唱震醒。
震聋发聩啊,眺望你的路途。那是高一的班级,负责指挥的女生面对身着黑衣黑裙的同学舞动她的双手。所有人的法语都只是勉强可以听的音调,声音并不大,但是我似乎感到一种十分努力、很有热情的声音。没有文艺委员会在班级合唱选择难度高的歌曲,排练的人一定会自取其辱——但他们选择了这一首,而且用并不十分动人的嗓音将它唱了出来。
那时小小的我觉得,升上高中之后,我便会成为这样夺目,闪耀的大人。我向来要稚拙地说自己喜欢《放牛班的春天》,遵循一种非常原始的冲动将它看了五、六遍,没有任何多余的考量,也并不存在文学少女的仪式感。我就只是基于原始的激情爱它,从没深思过那个电影世界提供给自己一种怎样的价值。
但是,我升上的高中其实没有一个能容纳全校同学的大体育馆。自然而然地,也没有什么班级演出了。大家都自顾自地活着。我没有像那样唱过任何一首歌。
破坏时间的线性感受是悼亡写作的必然。因为你死去了,现在和未来被彻底改变了,某种我曾经以为一定不会消失的东西彻底消失了。死对你来说是一个瞬间的动作,但对活着的我来说成为了永远的现在和未来。我就要在这种痛苦得无法忍受的世界里生活。为了我能继续活下去,为了你能继续活下去,我不得不把过去的记忆强行拖拽到现在和未来,那一瞬间,时间的线性感受被破坏了,时间变成了某种封存着等待着被打开的房间,这是你们称之为意识流的本质
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真正意义地活在现实中间。总要摸摸路边的东西,好确定自己就在这里,不是在经过别的地方,睁大眼睛好看清秋天的空气。像半夜突兀地清醒过来,但是拒斥着,且感到孑然。
觉得搞艺术的人都是具有强烈欲望的人。
我还记得童年时分我如何画画:把我所有的参考材料,绘本、图鉴、故事书,十几二十几本地展开叠放在桌子上,要小心它们不要倒塌,还要露出每一页折角的喜爱的部分,只留下将将好摊开画纸和彩笔的空隙。然后,近乎贪婪地,如饥似渴地在所有书页上扫视,在白纸上画下所有喜欢的部分、柔软甜美易吞咽的词汇、焕发着夏天色彩和甜香的糖果糕点、有新塑料味的精细机械结构、辉煌的节日、温暖的贺礼。
好像要填补内心空旷的饥饿——我把它们画下来,本能地将那些美好拆吞入腹。从笔尖下流泻的触感将我淹没,我置身于秩序和美的世界,在黄昏的集市里散步,空气中传来旧日斯卡布罗的歌谣,还有长长的汽笛声。
在现实中有多么笨拙,在那个广阔的世界中就有多自由。在那里我已拥有,且不感到饥饿。
我对琼瑶写爱情的观感很一般(我对所有爱情小说都不太感兴趣),但我非常能理解琼瑶笔下的爱情为什么都那么幼稚不真实、又那么绝望用力。
一个喜欢文学、严重偏科、社会适应不良、心思细腻敏感脆弱的小孩,和粗粝的控制狂父母相处,是非常受罪的。这也就好解释,为什么她笔下那些社会化程度很高的大人(从旧式家庭里的家长、到张牙舞爪打小三的正妻)都这么面目可憎没人味欠揍,而她所描述的爱情和男主,又是那么华丽、浪漫、叛逆,却根本不接地气。因为后者在本质上不是爱情,只是巴啦啦小魔仙的魔法棒,挥一挥,就可以让前者滚出她的生活。
(我为什么能感受到这个?当然是因为,我也是这种跟社会跟控制狂父母仇深似海的玻璃心文科少女啊!)
所以,我认为,《还珠格格》在琼瑶作品中最少争议、最有人气、最经典,这是理所当然的。这确实是她的巅峰之作。那个伤心愤怒的小女孩,终于找到对抗坏大人的正确路径:
——不是爱情,而是,很多很多活得真实炽烈的小孩子,一起红尘作伴潇潇洒洒,一起纵马奔腾踏碎那些神圣虚伪的宫廷规矩,大说大笑、真爱真恨,奔向自由。
和朋友倾诉了好多
心情变得爽快很多了,谢谢我的宝们给我的祝福
胸膛从空落落的状态被填充进了力量。是这样……也可以获得幸福感……
由衷地为我拥有这样的友人感到幸运,我现在就是需要着她们的陪伴,让我知道会被回应的安心的陪伴。我也很高兴自己终于能对不能启齿的感情,我不接受自己的部分说出口……好宝宝……好宝宝!(我们都是)
存一存聊天记录w
又看到好东西的宣传。虽然之前和一位不喜欢它叙事节奏和表达方式的朋友聊过一些,我对它拥有了一些正面和负面的猜测。但仅就这些好评的方式而言,它应该是一部审美角度来说很美的片子。我想去看。
- 做梦
- 泛神论者
- 刻板印象
- enfp 愚者正位 大龄中二病持续未愈
- 吾心之居所
- 我的国
- 幻想朋友
- 祂叫小影子,请保持尊重:)
Arion/关关🍁
20+/旋转飞碟冰淇淋拼盘一位里面请——
掌管宇宙飞碟的自由自在小彩狸,守护名为萨摩守的藩地。只记日记,偶尔读书。
一般路过潇洒小登。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