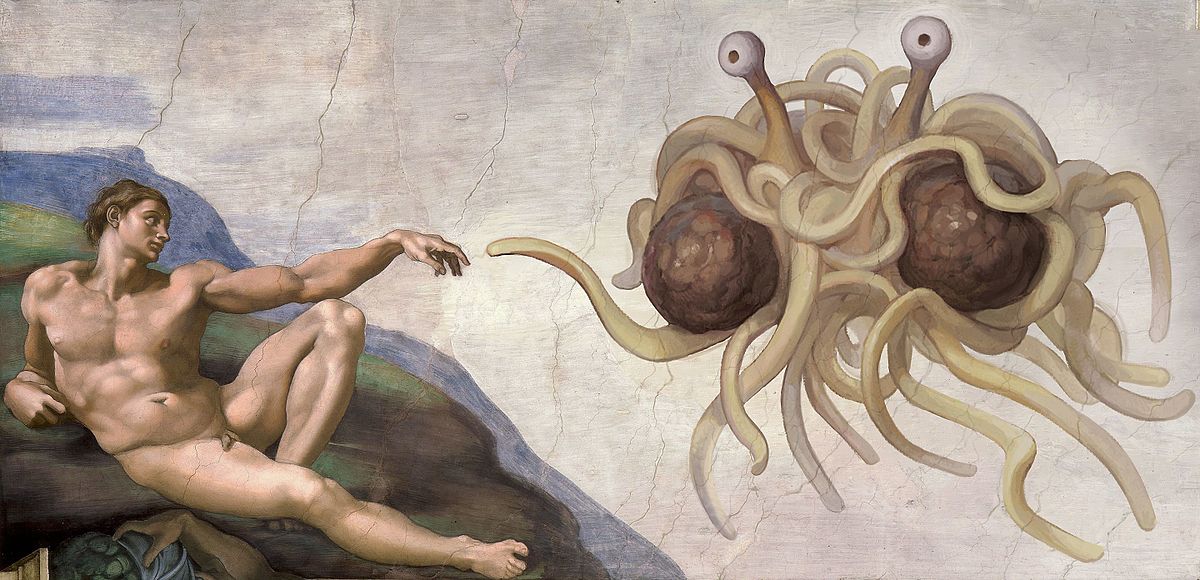我们都是半成品,父亲,半生不熟,在这个无穷尽的垃圾巨堆里迷失,流浪和误入歧途,杀戮和乞求原谅,在你的梦里躁狂抑郁,父亲,你没有界限的梦我们已经钻研了一千次还要再来一千次,就像拉美侦探迷失在水晶和泥巴的迷宫,在雨中旅行,看见电影里出现老人呼喊“龙卷风!龙卷风!”,最后一次观看万物,却没有看见,就像幽灵,就像井底的青蛙,父亲,都迷失在你乌托邦之梦的悲苦,迷失在你声音和深渊的丰富,躁狂抑郁在地狱无边际的病房里,你的体液在那里被烹制。
——《文学散步》
寄信水母
给友人一段小话,记录免得忘却。
听了你的话,去读辛弃疾。
念到水调歌头,「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突然像一道闪电劈过我,大江东归,流去滔滔,没有尽处,没有归路!突然明白你在课上讲的「让一切过去都透过我们的身体」(大意如此,抱歉记得不清,只对透过二字印象很深)究竟何意。难述我心中所感,记得你的故事盒子上写着,the river of life……只觉脑海一阵激荡,化作眼泪。
你的生命,也每每被这样浩瀚的事物所穿透、震荡吗?这样澎拜,这样宽广?
咱们东亚小孩找爱意都是从零开始找,我今天一点点思考是,就是我原谅我的父母,我也不信任他们能给我我需要的爱。我要的是相互信任、无条件的、稳定、宽厚的爱,他们没有这样爱人的能力。
我自己在茫茫人海里寻找爱意,从自己找的朋友和她们的家人身上榨取爱意,将自己从极端匮乏变成中度匮乏(?)
想起小时候我爸给我零花钱,说女孩要富养,不然长大男的一点小恩小惠就把我骗走。其实富养需要的是富泽的爱意……没有体验过合适的爱真的会被一些边角料爱撞昏头的。
我去年去意大利,回来直接抑郁,是因为我在友家里过了一个多星期,我在她拥有的爱意支持网里浸泡,她妈妈会给我很长的拥抱,给我们准备三餐,她们家里人不吵架,不会高声对骂,她的朋友会在晚上聚在她家里跟她嬉闹,而且陪我玩游戏。我都很恍然感觉此生没有被这种温柔地对待过。我当然有很多朋友,但我没有过这样,就在我身边,会很温柔拥抱我的人(而我对她来说甚至见的时间加起来没有一个月,她不会英语,我们也没有办法见面对谈)。
宇宙水母·五月上旬综合
五月是奇妙的月份,虽然工作量增加压力却内化,胸口不时憋闷心悸,却不再情绪崩溃了。四月每周都定点经历的郁结情绪成了一种稠稠的结块的精神状态,遇到事情会变成愤怒肉松或者假笑薯片,沉沉地压在心上,变成可以盘算也可以意识到的,情绪。
我的情绪察觉能力进步了好多,调节能力也增长了。不知道有没有气温气候的原因,反正觉得一切都很厉害,并未雨绸缪地害怕冬天。要怎么准备过冬呢。
声响
天哪,我的灵魂
发出一些奇怪的声响,
类似一些劈啪声,
仿佛夜晚
房间里的家具,
有时会让你觉得有什么人在柜子
或吸墨器里走动。
天哪,兴许真有什么人
在我心里走动,
每次睁开眼睛,
我都会鼓足勇气问道:
会是谁呢?
兴许月亮
企图劫持我,
从窗户跳进了房间,
用梦的美丽镶饰
让旧家具如幽灵一般
咯咯作响。
聆听水母
姐姐:那些艺术家需要把他们脑海中的自我与偏执的想法发挥到极致,所以往往对外界要求很苛刻。而我作为工作助理时,就是满足他们、被他们发泄情绪的人。
我:噢……
渐渐意识到那些尽情挥洒的人之外是无数无数工作者给予的托举,正因如此,那个辅助性的世界才会有各种各样能干的人为人所知。也是因为这样,姐姐才能自信地对甲方说,“没有我们的宣传,你也没什么了不起”。在金钱近乎不限量流通的地方,每个工作领域都拥有最为闪闪发亮的角色,他们的骄傲也是对自己能力的认可,对自身名誉的守护——同时也成为社会性的拥趸。
我总是心存妄念,但是在这样的世界也许会被渐渐地融化。曾几何时,我也储蓄着那个高度膨胀的自我这样不断生长,并以为自己会走上某条路。如果我选择了一条岔路,那么,我还能回去吗?都说人生是充满弹性的,但自我的复归……也并不尽然。社会性是某种强奸人脑子的外附本能,铁链勒久了,也许会和血肉黏连在一起。那样的自我还是自我吗?
然而这或许只是一个固步自封的自问自答。个体探索的极致需要外部能量的摄入,停滞不前只会一次又一次地产生同质化的作品和问题。社会化不存在唯一的修行之道,也许另有可以保持警醒的方式。想起九井老师,她对外界的观测又何尝不是一种社会性的极致……那也是个性的一种啊。可惜的是,似乎我生来便比较像图丁兄妹。选择不适合自己的路,肯定是一种打击吧——要想探索这个世界,手段是必须的,对意识警惕心也是必要的,毕竟我们总是在为某种标签而付账的样子。恰如我从前根本不买谷子这次却选择购入,是希望被所爱之物环绕,希望获得一种群体性标志的维护,还是希望观测构成它们的材质呢?或许兼而有之。
一切事无需一定有意义:但是我不想轻易被裹挟。
- 做梦
- 泛神论者
- 刻板印象
- enfp 愚者正位 大龄中二病持续未愈
- 吾心之居所
- 我的国
- 幻想朋友
- 祂叫小影子,请保持尊重:)
Arion/关关🍁
20+/旋转飞碟冰淇淋拼盘一位里面请——
掌管宇宙飞碟的自由自在小彩狸,守护名为萨摩守的藩地。只记日记,偶尔读书。
一般路过潇洒小登。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