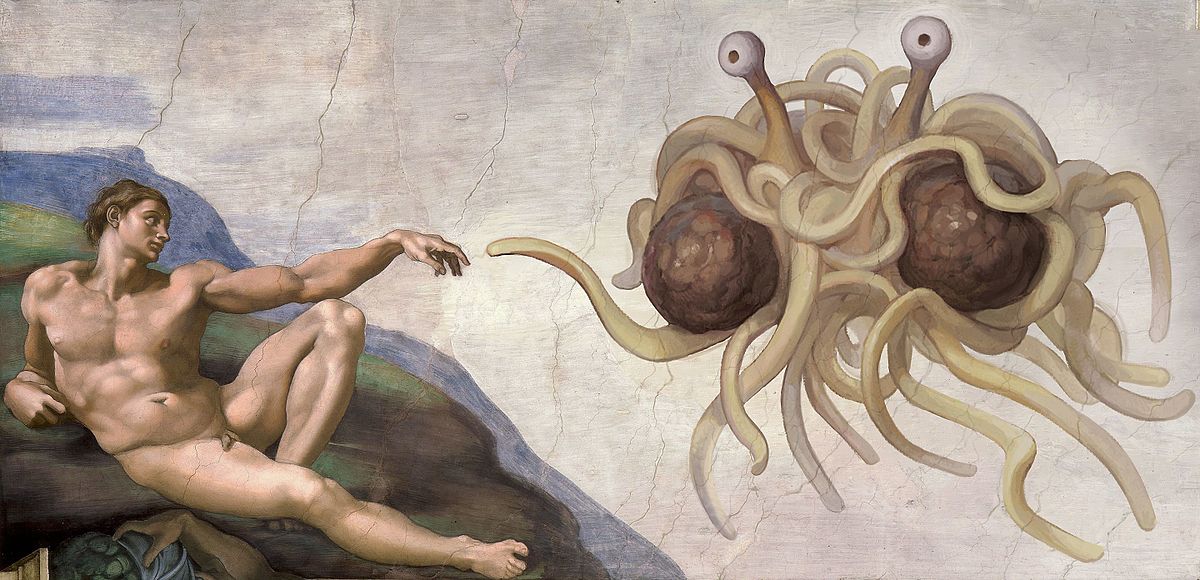浮沉水母
心好痛。
还是很难处理她数天不理睬我这个事实,尽管已经知道有些关系只能到这一步,而我也答应不因为她的不告而别而感伤
但是实际做来,仍旧困难——渴望受到对方的心的呼应,渴望对方对我细小的探询产生反馈,所以当我徒劳地碰撞着空气,胃会纠结成一团,心脏怦怦响,极度迟缓地榨出汁液。我知道那里有一点点震动的反馈,但这是不够的。我十分饥饿,十足贪婪,在沉默里养成了对虚幻之物索求无度的习惯。这种疼痛是因为滋生出的情愫不同,或许——
但是叫猫在你身边舒展肚皮和让猫回响你的吵闹和需求,终归是不能共存,只能看性格与际遇的事情。所以说爱是恒久忍耐……爱是选择,也是相互承受。
我选择了聆听——选择待在对方身边——就要承受我面对的是一个直视其他地方,默默处理自身伤痕的人。我或许也对这样的生活感到麻醉和上瘾,大概我也是一个抖M。
昨天和友人一起看了法扎,大概知道自己为什么一眼迷上了萨列里——但任何人都知道的,在历史的事实里莫扎特从不回头。我被那种惨烈的没有可能所割伤,想起今天冰老师的直播。
……爱是有尽头的。这令人惘然。空空消费气力的爱会消耗我的青春吗?
“我们用欢笑,嘲笑了死亡,愚弄了时光。”
——纵情生活
黄色水母
人是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赋魅的
但是我现在真是冲多了肾虚
……原来肾虚真会腰疼!!
一些 pal 手帐的有趣用法(因为是网页保存的没有小红书 ID 水印了 ![]()
比较感兴趣的还是月视图这块。把睡眠(起床/上床)、运动、精力情况平行放置,可以给自己很多窥视情绪变化的空间。
最近几次 panic attack,或者突然发生的抑郁情绪浮现,后来我都意识到是和当时身体/精力状况有很直接的关系。也不是说焦虑的起点是假的,但比较像是把八公里外的一个树坑变成了下一脚就会踩下去的深渊,这可能是人类大脑的特点。是要考虑树坑的问题啦,但不应该受到这么大折磨 ![]() 能马上意识到的话,尝试下来是可以把意识(我现在遇到问题了)和感受(被强烈低落情绪扼住)分开,如果能借助外力比如安全他人的帮助,就能缩短受困周期
能马上意识到的话,尝试下来是可以把意识(我现在遇到问题了)和感受(被强烈低落情绪扼住)分开,如果能借助外力比如安全他人的帮助,就能缩短受困周期
很久以前友给我讲过一篇同人,虽然是我不吃的cp但是这个故事的回味实在是太悠长了,以至于我记了很久
开篇还是比较日系经典的俗套设定的,就是说a和b其中一个人濒死,具体忘记了但是总之a用了一个什么办法让他们两人的意识进入了一个无限循环的一日世界,这个世界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但是两个人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每一次的“今天”都十分满足
但是有一次a从超市里买了竹荚鱼回来,在路上和b商量说怎么吃呢?b说用醋渍吧,a说好,因为醋渍竹荚鱼是要腌制一晚上的,所以就把鱼放进了冰箱里,心想明天就可以吃了
但就是因为这个简单的动作,因为对“明天”产生了期待,这个世界的秩序就崩坏了,无限延续的幸福的“今天”就这样结束了,a和b的意识被抛回了凄惨的现实中去。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有一种……与“不要回头看”对照的寓言故事一般的意味。因为对明天产生了期待,也就意味着开始渴求更多,正是因为将现在拥有的幸福当作了理所当然的东西,才会认为这份幸福明日也会自然而然地延续下去。可是人就是这样不知饱足的生物,得了一便想要二,拥有便会产生贪恋,但贪恋就是通向失却的钥匙
又回想起来疫情期间集体注射疫苗的事情。
我们本地的室内公共场所是体育馆,那时还是冬天,全校师生集体来排队。我讨厌死了口罩的触感,根本不管父母的叮咛,总是偷偷把它揪到鼻尖下面,就这样,呼吸处还总是连接着一片湿而冷的水汽。
激光打完注射卡,捞起左臂的袖子(那时我还在高考,右手要留来写字),医护人员掰开疫苗小管有清脆的咔嚓声。我其实怵头,回想起小时候父亲说不看就不痛了,少年脾气上来,便逼着自己直视,脑袋僵直得像颗强扭的瓜。很多人都说打新冠和狂犬疫苗一样,打完痛得使不上力气,但我只有第三次肌肉注射极痛,由于自诩很会忍耐,就风轻云淡地硬撑,还要去主动招呼同学聊天。
注射完要在场等待三十分钟,不大的体育馆中间摆了很多塑料凳子,饮水机有温水,所有到场的人不知为何都在狂喝。那时候,体育馆的木地板经过累月的踩踏带有一种温润的油黄褐色,木块松动,行走中和鞋底磕碰出硬硬的嗒嗒声。踩在那样的地板上,恍惚中觉得好像正在参与一场大型活动——尽管周围围绕的不是帘幕而是白色个隔离屏风,还充斥着消毒水和体育场胶皮的味道。
像是初一时被组织起来的元旦联欢。在中学的大体育馆里,我们摩肩接踵地坐在塑料凳上,巨大的幕布被钢筋吊起,在舞台上放射出深邃的阴影,空气潮热,人们突如其来地为闪亮登场的演员们鼓掌。那样的演出颇有抽离感,我不时被演出的吵闹带跑,又低头翻看自己带来的小说和作业——然后被一首《vois sur ton chemin》的合唱震醒。
震聋发聩啊,眺望你的路途。那是高一的班级,负责指挥的女生面对身着黑衣黑裙的同学舞动她的双手。所有人的法语都只是勉强可以听的音调,声音并不大,但是我似乎感到一种十分努力、很有热情的声音。没有文艺委员会在班级合唱选择难度高的歌曲,排练的人一定会自取其辱——但他们选择了这一首,而且用并不十分动人的嗓音将它唱了出来。
那时小小的我觉得,升上高中之后,我便会成为这样夺目,闪耀的大人。我向来要稚拙地说自己喜欢《放牛班的春天》,遵循一种非常原始的冲动将它看了五、六遍,没有任何多余的考量,也并不存在文学少女的仪式感。我就只是基于原始的激情爱它,从没深思过那个电影世界提供给自己一种怎样的价值。
但是,我升上的高中其实没有一个能容纳全校同学的大体育馆。自然而然地,也没有什么班级演出了。大家都自顾自地活着。我没有像那样唱过任何一首歌。
破坏时间的线性感受是悼亡写作的必然。因为你死去了,现在和未来被彻底改变了,某种我曾经以为一定不会消失的东西彻底消失了。死对你来说是一个瞬间的动作,但对活着的我来说成为了永远的现在和未来。我就要在这种痛苦得无法忍受的世界里生活。为了我能继续活下去,为了你能继续活下去,我不得不把过去的记忆强行拖拽到现在和未来,那一瞬间,时间的线性感受被破坏了,时间变成了某种封存着等待着被打开的房间,这是你们称之为意识流的本质
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真正意义地活在现实中间。总要摸摸路边的东西,好确定自己就在这里,不是在经过别的地方,睁大眼睛好看清秋天的空气。像半夜突兀地清醒过来,但是拒斥着,且感到孑然。
觉得搞艺术的人都是具有强烈欲望的人。
我还记得童年时分我如何画画:把我所有的参考材料,绘本、图鉴、故事书,十几二十几本地展开叠放在桌子上,要小心它们不要倒塌,还要露出每一页折角的喜爱的部分,只留下将将好摊开画纸和彩笔的空隙。然后,近乎贪婪地,如饥似渴地在所有书页上扫视,在白纸上画下所有喜欢的部分、柔软甜美易吞咽的词汇、焕发着夏天色彩和甜香的糖果糕点、有新塑料味的精细机械结构、辉煌的节日、温暖的贺礼。
好像要填补内心空旷的饥饿——我把它们画下来,本能地将那些美好拆吞入腹。从笔尖下流泻的触感将我淹没,我置身于秩序和美的世界,在黄昏的集市里散步,空气中传来旧日斯卡布罗的歌谣,还有长长的汽笛声。
在现实中有多么笨拙,在那个广阔的世界中就有多自由。在那里我已拥有,且不感到饥饿。
- 做梦
- 泛神论者
- 刻板印象
- enfp 愚者正位 大龄中二病持续未愈
- 吾心之居所
- 我的国
- 幻想朋友
- 祂叫小影子,请保持尊重:)
Arion/关关🍁
20+/旋转飞碟冰淇淋拼盘一位里面请——
掌管宇宙飞碟的自由自在小彩狸,守护名为萨摩守的藩地。只记日记,偶尔读书。
一般路过潇洒小登。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