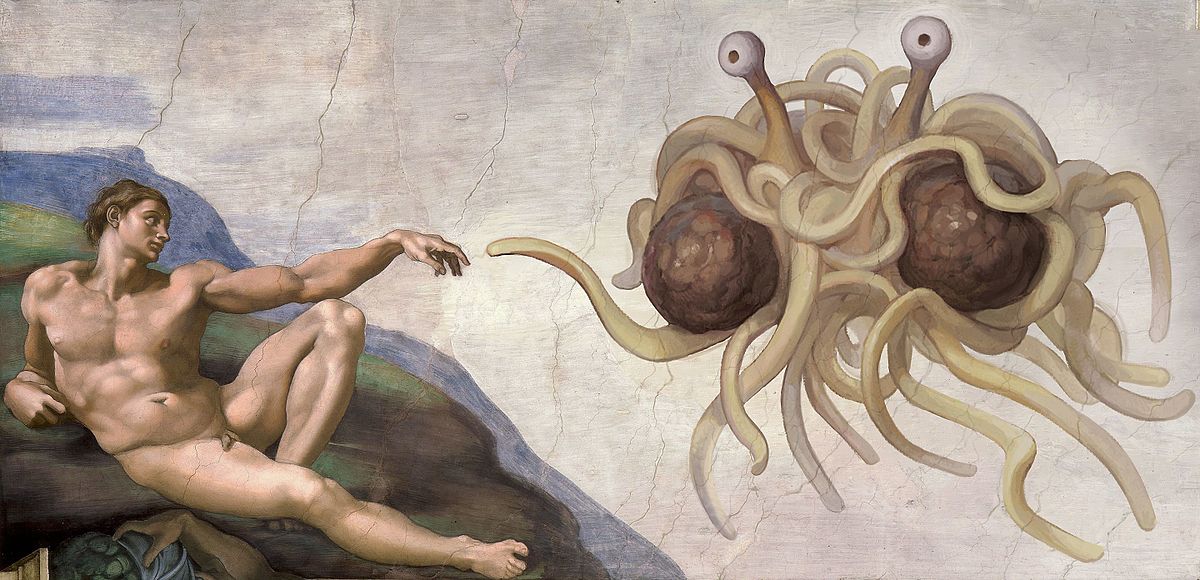《鹤唳华亭》的齐王妃,回回出场都在争风吃醋,乍一看工具人属性很强。中书令倒台后她在齐王的事业版图里已然无用了,她又无子嗣,却毫不为保全自身而收敛,依旧坚决反对纳妾。可当她看到张陆正的次女着嫁衣跪在王府门外,齐王因为被逐愤而拒见的时候,她不忍心了,说外边冷,让她进来。
这一刻她对另一个女子产生的怜惜与共感超过了作为妻子对夫妾的嫉妒,已经胜过无数为了男子戕害其他女子的情节。
尤其是她未必知道张陆正被判刑后次女惟出嫁才不至受累,她那时是内疚与悲戚,她看到除了自己还有另一个女子愿意随齐王去偏苦之地。她虽为次要人物却也是悲剧一环——所求并不为过,偏偏得不到,还不是冲突之下被夺走,而是隐忍地自己放手。
摸
一日几番推倒重改夜里用手机一看还不如不改
#春天的十七个想死瞬间
对比那种一旦发生便无法逆转的事件——如激烈冲突和伤害,无数个毫不起眼的瞬间积压导致了结果才是多数情况,是想不出具体原因但方方面面都浸透其中,处处不见的惊悚——设定情节时也该想到,生活不是非黑即白般明确,一种感情并不凭依某个特定的情节,一种转变也并非由于某步出乎意料的棋——除非是前者那种避无可避的劫难。铺垫,还是铺垫。
念叨了几年赏花因为瘟疫和见不着人一直后延,已然无心了。友之前提过郁金香园,方才再提植物园,想及她搜集的讯息,忽地觉得,友为了让我活下去比我还努力
#春天的十七个想死瞬间
小女孩并排凭栏撕碎絮状的糖云,指缝飘落的糖掠过绿头鸭的羽不见了,白羽翕动重彩的漪,摇出缕缕水光抚过亭身,亭下女孩的发流光滟滟,女孩眼中歪扭的湖剪开,一片水囚住湖心亭。
#春天的十七个想死瞬间
月半前约了友五月去看维多利亚艺术展,主要想看看利物浦博物馆运来的展品,毕竟暂时没机会去本土,欸好想逛大英博物馆(的仓库)——!这个时间段还赶得上看琥珀展,以及馆藏铜镜展周期好长不愧是本馆藏品,可惜叙利亚文物展尚未开放
高中地理唯一的乐趣是试卷上偶尔出现竹丝扣瓷一类手作,我可以从这一点遐想从前的小物,像在省博看原木家具展一比一复原的明清房间布局,在每一个房间前驻足良久,对照注解想象前人在这空间里的日常。
刚看一个花篮糖画的制作视频,想起很久以前看谷雨中国和李子柒,走马观花仓促窥探一些存在的事实便离开,印象不比展柜玻璃上的映象深刻,但仅仅这转瞬间的接触也觉得好美啊……理性上我知有些在当时并非全民皆可享受之物,有几场出口文物展的展品绝对只出现在富裕阶层家中——但感性上仍觉得好美,不会想这是资本挤压的血,我据以想象的世界是少数人的世界。退一步说,也许连朴素的年糕在走出本乡后成为折现的商品,本乡人反不吃了。一细思便预设了许多看不见的伤口。我为何因一个糖画浮想联翩,因为长大后我再没在街头见过了,而这本是寻常物。
叨叨画
今天拿起赝品组的插画看了许久,知道该怎么改但不想改,疲惫了。和这张一套的另一张迟迟想不出新构图(旧构图画过两版草稿,都不好),那张集了最难画的俩人,又要兼顾他们的关系性,纯属给自己制造难题……
叨叨画
最近一直画路德,但亚瑟就,实在想不出画他什么好,设想里路德属于普通美人(?),亚瑟属于那种知道他漂亮但常被这种漂亮蒙蔽了美的部分的美人(要不要看看你在说什么),相较下路德比较好画……
夏洛比他更难画,她和路德跳舞那张,我抠了好多天她的脸抠不出满意的。不奇怪,我从初中开始画她,始终画不出想象的模样。如今至少比以前能表现一点神情气质来,毕竟很长一段时间我画什么都没有情绪。)我以前用阿佳妮戏中的痴狂状来比拟,可她太精致了,夏洛就始终沾点莽气,粗糙,某些时刻甚至不大漂亮,但她有种独特的迷人。好比我以前看《卡萨布兰卡》不觉得男主角好看,但真迷人啊(所以她是不让人觉得漂亮但会不自觉被吸引到觉得好美的非传统美人(……
也许用无性别感形容比较恰当……
和路德跳舞那张从线稿到第二次上色都让我觉得她好凶——毕竟情境设定是两个人都在警戒状态,只是路德笑里藏刀,她连笑都不赏——可单拎出来又违和,调了好多次,放大看挺美,缩小有问题。下午又改了一版,拿给我妈看,她说我最近的画都不像我的画,我:这可不正在尝试别的玩法嘛。如果按草稿来简单铺个底色画成偏欧美风的插绘那确实早就画完了,问题是不大想那样画,想碰碰壁。正因为不会画才会在再刷到类似效果时留意别人怎么画。
现在这张的情况是,我想摸索她的脸,我想在这张脸上表达画面上没有展现的东西,但所有这些合在一起我给整不会了,然后越改越丑,改久了原型崩溃,别说表达什么,连正常五官比例都画不出来了。但又很想画,非常想画,只能每天摸一会又不满意地关上。
一言以蔽之,想得太多,基础太差。
每逢雨天便想阿止何以喜雨,兜兜转转结论是几率小于等于不喜欢。
此处延伸的觉悟是:我得警惕把自身喜好加在人物身上。仅个人而言,有时好恶确与个体经历相关,我之经历不可复制,他们亦然,一旦将设定置于他们的生活便违和。明知如此仍难避免的原因,一是人更容易从长期浸淫之物中获取灵感,因熟悉而写得真切,这是诱惑;一是在观察了解不够的情况下,人难以想象他人的好恶形成。不是所有好恶都有原因,有原因也不是主体之外的人皆能理解,遂非不为也是不能抛却自身视角设想他者。
扯回来,需要从一些切入点重新认识我写的人们,我扳着指头估计他们没几个会喜欢阴雨天……
选角第二弹
格蕾丝·萨特菲尔德:凯瑟琳·泽塔琼斯(《佐罗的面具》《偷天陷阱》)
最初光看脸想定索菲亚·萨特菲尔德,但看她在《佐罗的面具》里跳舞乱了长发后觉得适合格蕾丝一些(这么说埃尔伍德得是金发才行?
夏洛特·柯黛:(没找到演员名字)(《Kin》)暂定
宁沅:陈红(《聊斋》《霜叶红似二月花》)
原本想何赛飞,她演妙玉的气质像,可我又不能用妙玉来剪师母。蒋勤勤陶慧敏小家碧玉些不太压得住,何晴给我一种大唐盛世的滤镜……后来看到陈红演连城晃秋千以及霜叶里的张婉卿,感觉可以分别是少女时期和嫁人后家道中落的模样(虽然离民国还有整十一年(主要是陈红在这两部里太好看了我狂截图
假如给我小说选角(指剪视频
夏洛:莫妮卡·贝鲁奇(《情事》)
最开始想过阿佳妮,演《阿黛尔·雨果的故事》还偏温婉,年纪稍长演《阿道尔夫》《玛戈皇后》的气质状态就很对味了,然而她眼睛大得有惊怖之感,癫狂嗔痴有余,气势不足,和镇静周旋的棋手不搭。
最近觉得莫妮卡·贝鲁奇演《情事》时期很可以,她比较高,骨架体态方面贴一些。可姐姐接的剧本让我不知挑哪一出,感觉都很色……
伊丽莎白·布兰威列:薇诺娜·瑞德(《纯真年代》)
在《吸血惊情四百年》的经典绿色裙装不错,在《纯真年代》的妆造更配
安内特·菲林格尔:罗克珊·梅斯基达(《昔日情人》)
我连哪个镜头对应哪段情节都想好了,然而没找到片源
人还是不能被文学史给骗了,至今摸的苏诗写得好的都味苦,我估计柳更苦……以前 老师说维诗是山水那一挂里最不接地气的,可不,仕途平坦,年老还能上书皇帝与弟弟相互帮衬,除了安禄山那阵被囚禁了基本没受什么折磨,何况还有诗为证没被诟病出仕伪朝……平时休沐约着友跑去辋川别业玩,夜里独坐参禅,完事还叨叨了在地里苦的渊明……就,别太过分了啊
我不会写甜文已经到了友说以为我在写梦境,是一出随时醒悟的骗局的程度。不知是我写得不对劲,还是她对我文的印象早定格在悲剧;难说是由于阅读传统还是我读完《人生道路诸阶段》也没解答的那个问题(尽管读的时候我也没寄望于借哲学解决问题)。
我的感知是他始终困于退婚事件,抑或他在反复书写退婚原因以抒发。这里阿克是否喜欢前未婚妻本身不重要了,他陷进一个死胡同:因为我不知何为爱,所以我不能进入爱——如开篇的大学生所言。
有时我也像那个反复诘问究竟何为爱情的青年,「为何围绕该命题的文学作品源源不断,却从未有哲学家探讨什么是爱情」。
我写恋爱会不由自主往悲剧方向走似乎根源于我并未相信爱情,或者说尚未看到一种让我信服的爱情的形态。
我厌恶《一位陌生女人的来信》,首先心理描写并没有给我惊喜,更主要是,她整一个献身实际是通过不断复制过去的自我来构建「我」的过程。她第一次跟作家上楼(之后上床)前的描述是「啊,这是我从小想到大的楼梯」,诸如此类的描述随处可见,她很多时候的注意点并不在作家本身而在过去那个时间点。
写到这重读了《窄门》第七章至结局,忽觉和我以前想的不是一回事。我起先过分放大了阿莉莎更换书架上的书这一节,以为她在他和上帝间选择了成全他,为了让热罗姆不再崇拜她而「自甘堕落」,却又无法接受自己的伪装才郁郁而终。可我现在发现她换书和做家务皆是为了逃避热罗姆……她始终没放弃过上帝,我当时是不是因为《面纱》太在意「偶像坍塌」了,在热罗姆当时的角度看似乎存在这一点,但不多。
那很遗憾,也好在不是。现在人都从关注他人回归到关注自身了,向神灵献祭式的爱情终于不再被歌颂。
另一种形态是,「因为那个人和我很像/有很多共同爱好聊得来,所以喜欢」。不得不提友人拉我看的《花束般的恋爱》,我一直想:喜欢一个和自己很像的人难道不是变相的喜欢/肯定自己吗?此外人类复杂如斯,两个人的交汇处其实很少,假使对于对方身上和自己不同之处视若无睹,实际仍未真的接纳,不过是从对方身上捕捉自我的延伸——就像电影的男女主对于对方喜欢的博物展/热气球并不感兴趣。这里重点在于,我可能不太了解你喜欢的东西,不过我愿意为你去尝试了解——喜不喜欢另说,至少我试过了,而非搪塞或装作感兴趣让对方误会。
至于别的,婚姻,在我眼里已经和找合伙人没多大区别了。你说搭伙过日子过了几十年的老夫老妻,外人又怎知那是撑过了七年之痒,还是财产分割或抚养权之类太麻烦所以凑合着过呢。
就是说谈个恋爱途经无数个滑向悲剧岔口,所以写悲剧性是很容易的。可一路向前能走到什么地方,我至今不知道,至今不会写。
进度记录
走廊也被我纳入小作坊的工作区划了。
乍一测缩水率好高但按比例摊平就还好,只是担心是否够用。
以及,不知哪一步骤没调好,染三次和染五次的小样风干后区别不大,明日再加热看看。
我忘了二月没有三十天,偏偏谜之有自信能做完整个系列,只是导师那边得再探探口风。
本号是用来关注友邻的魂器,主号在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