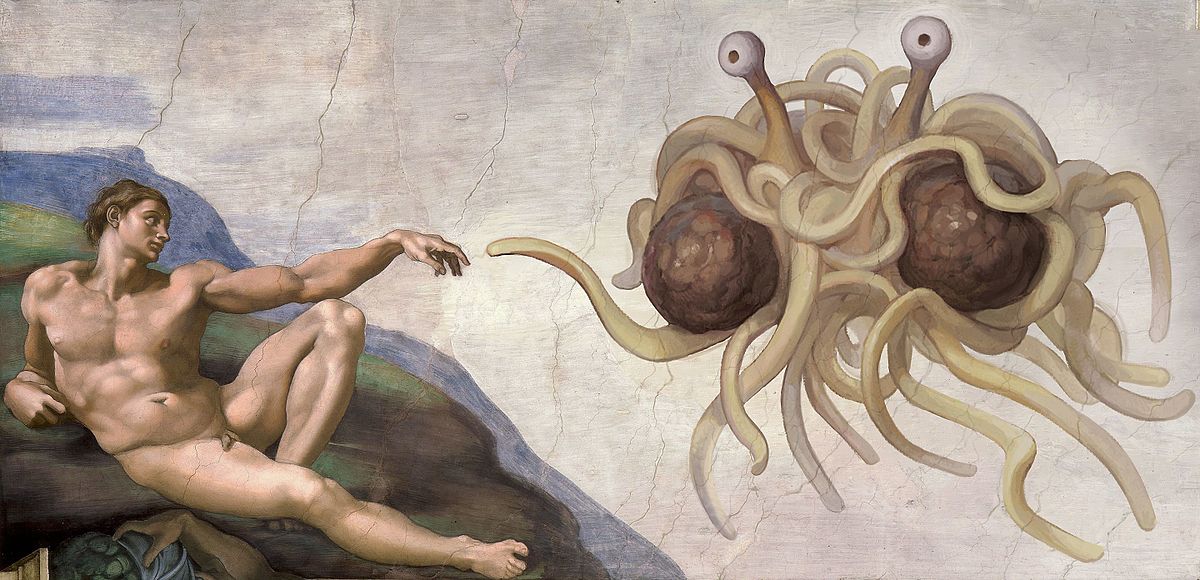我觉得该不该仇恨具体的人这个建议真不好说,因为真要说仇恨具体的人,有的人比如我,在母亲这儿受到的直接伤害比在父亲那儿多,在女性圈子里受到的排挤孤立和霸凌也在比男性那儿受到得多,而且是成倍数的多
性别隔离的社会文化下会让人不得不根据指派性别,来作为自己的第一个也是最长远的社交圈层,那么在这个圈层里接触到的同样指派性别的人所给的直接伤害绝对比其他地方给的更琐碎和繁复,每天的摩擦如果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不用你教她也会恨具体的人。
所以如果有的人生活在从小就被其他女性胁迫似的教导要奉献自己成为附属品、甚至甘愿充当男权社会的打手的环境里,在这些具体的女性面孔对她日复一日施加暴力的前提下,在她看不到更长远问题时,会让她比其他人更渴望钻入真正伤害她的问题中,她会更渴望结婚,加上她被暴力折磨到低自尊和低期待值,她会认为男人十分普通平庸的好处也比原生环境中日复一日的欺压更好。而且最糟糕的是,结婚这个糟糕的选项,很多时候却真的能(在至少一段时间内)缓解她最急迫的情感需求和对自主权力的需要。
而且还有一些时候,人不去也不能去仇恨具体的人是因为这是她为数不多仅能遇到或者最后可以依赖的东西,比如我有一些les朋友她们遭受过来自伴侣的家暴,甚至有的还很频繁,我认为性少数人群遭受家暴的问题是复杂而且难以开口的,它并不像异性恋社会议题下的女性,总能找到一张可以去憎恨的男人面孔。在女性酷儿的生活问题中,男人的面孔,尤其是顺直男人的面孔有时候往往是模糊的,甚至很多时候这些问题是可以避开的,但亲密关系里却不是,而这些冲突总是比上班被男同事碰掉饭盒更能留下伤口。
人的生活是这样的,不是某种应承的模板和套子,即便是同样都被父母家暴,不同的个人经历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很多时候,女权让人痛苦,因为身为指派女性必须,以及不得不反直觉式的去相信一些从没有拥有也没有见过的东西,思考也是痛苦的,这个过程让人不得不恨很多原本不想恨的东西。
我现在觉得在海棠吃饭是在吃人血馒头,因为这几天的事情我才知道海棠为什么很多饭不好吃,因为很多人在海棠写文是真的在谋生,而不是追求情感愉悦,炖出来的当然不好吃,马斯洛需求理论,很多作者可能还停留在第二层,而我觉得炖得好吃的作者全都走到了第六层或者第七层,表现上来看都留过洋
其实我隐约能察觉一点,这几个星期沉迷骨科有点进去一本骨科文,评论区夸作者写得好我却看得毛骨悚然,因为太真实了,女主面对的困境太真实了
这本书是工作独立的异父同母哥哥和还在读高中的妹妹,妹妹有一个弟弟是家里的皇帝所有人都偏爱他,只有哥哥在乎妹妹……妹妹每天在家里被妈妈凌辱,穿个衣服涂个美甲都要被说是婊子勾引人,哥哥把妹妹从家庭里拯救出来,给她一个家,并且最新进展妈妈还病死了,同样也在作恶的爸爸和弟弟的凄惨也不过是妈妈死了没人洗碗家里很乱弟弟没人管,看了让人想大叹气。
就……一本书写成这样,那些细节太过真实太过刺痛了,真的有这个必要吗?然后作者又把这种痛苦变成性欲送给你吃,幻想一个不存在的哥哥成为自己的温馨港湾,哥哥这个身份足够亲近所以也足够安全,甚至哥哥开的还是书店!这种东西我又怎么吃得下?我不是没有良心的人啊……
我有时候经常说有些作者的文写太穷了很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现在想想可能这真的是她们所能幻想的极限了,一个爱人永不阳痿的鸡巴和一间房哪怕是租的以及一份足够自给自足的工作,太渺小的愿望,但幻想够小才有成为真实的可能……
【 #38岁女子放弃北漂住进养老院 :每月2000元包吃包住】近日,“38岁女子放弃北漂住进养老院”上了热搜,引发全网关注。距离她回到东北老家开启“养老”模式已经过去三个月,突然登顶热搜,她表示“挺意外的”。杨杨是一名编剧,在北京“漂”了十余年,合租房见证了她彻夜写稿的逐梦时刻,去年8月,一场大病促使她做出改变,转身走进故乡养老院,过上了暂无收入但有人间冷暖的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住进养老院的年轻人并非杨杨一个。封面新闻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她所在的养老院住进了一位00后,而在北京、长沙、成都、西安等地,也有“青年养老院”正在营业之中。
“北漂很难,编剧这条路也很难,很多时候赚不到钱,没有强大的毅力你没法坚持下去。”杨杨此前跟过剧组,时常凌晨三四点才睡,熬夜“肝”稿子成为常态。当病痛袭来,她开始反思。“生病的时候,我想的从来都不是写了多少万字,而是我去过哪一座城市,有没有真正的爱过我自己,真正休息一下?有没有去见见我的朋友,见见我的家人?”
出院后,杨杨收拾行囊,告别曾经誓要闯出一片天的北京:她需要一个安静、舒缓的地方调养身体。父母已逝,齐齐哈尔农村的老宅无人居住,独身一人的她婉拒姐姐弟弟的同住邀请。“我的身体情况不太适合和他们住在一起,因为需要早睡早起,加上神经衰弱,一点声音都会把我吵醒。”最后,她将目光投向了养老院:老人生活规律,饮食清淡,而且还有护工和医疗团队。
虽然病愈后积蓄不多,但东北的物价也是出了名的亲民:2000块,就可以在这座占地一千多平、有果树、有养殖场,还有孔雀和梅花鹿的养老院包吃包住一个月。
规律的作息和三餐让杨杨的身体逐渐恢复,同时,也让她在大城市里高高拎起的心缓缓落地。“北京有梦想,但这里的生活更有性价比,拥有了一个向阳的、独立的房间。”
在养老院的主流客户眼中,38岁的杨杨还是个孩子。“养老院(的入住人)以老年人为主,有八九十岁的,还有个102岁的,他们都喜欢年轻人。”杨杨所在的某养老院院长,今年76岁的张义告诉封面新闻记者。
初来的杨杨当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除了日常的关心问候,还有长辈对晚辈的各种投食:水果、点心,以及老人亲属带来的特产。这里温暖,却依然留有边界感,老人们对她说,“你看你这么年轻住在养老院,可是我不想问你,你一定有你的原因。”这种分寸感让杨杨得到放松。同时,与老人相处的过程中,杨杨有另外一种收获。
“住我对门的老人有一次凌晨三点半爬起来洗碗,把我吵醒,我倚在门框上问他,‘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他说‘我睡不着’。他笑了,我也笑了。我知道他很难受,因为他以前是个体育老师,现在却睡不着,而且行动不便。于是我说,‘那你以后白天别睡觉,晚上多睡会儿’”。
当杨杨不再和老人争辩,而是试着去理解,她急躁的脾气慢慢缓和下来。虽然手里余额已不够支撑半年房费,但作为一个编剧,只要有网络和电脑,她便能再返职场。和在北京躺在病床上还要码字时比起来,现在的杨杨已经乐观太多。“何况,我现在的身体不允许我焦虑,只要身体好、开心,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而且就算真的到了很困难的那一步,我还有亲人。这就是和老人在一起,我学会的豁达。”
杨杨把养老院当成了一个疗养院,她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标注:计划拍摄100位老年人真实的生活状态,无偿为老人写回忆录。而她现在也确实在着手做这件事。“我想成为一名作家,写这些并且发出来,就是想让大家看看真实的老人群体是什么样的,这个是我目前以及未来几个月想做的事情。”
如果说养老院的杨杨和00后学生是“入住个例”,那开在城市郊区或乡村的各类“青年养老院”则是年轻人的另一种主动选择。记者搜索北京、长沙、成都、西安等地,均有青年养老院在营业,场地大多设置在郊区,以周租或月租为主。
位于云南西双版纳的一家青年养老院在社交平台上热度颇高,薛佳凝也曾在此打卡。老板路先生是一名92年的环球旅行爱好者,半年前和朋友合作开启这家青年养老院。他告诉记者:我们只接收45岁以下、不带孩子的客人。
与传统的养老院不同,记者询问了成都另外两家“青年养老院”,得到的答案几乎一致:这个面对年轻人开放的院落,并不能完全满足入住者的食宿、医疗、生活等需求,通常情况下,“青年养老院”更像是一个平价版的青年民宿:提供住宿,组织活动,供年轻人短暂休憩。
“对于在城市里打拼累了,想要短暂休息的年轻人来说很有吸引力,所以现在到处都有人在开青年养老院。但做这行根本不赚钱,因为你的目标群体本质上就不是为了消费。”路先生说。
当青年住进养老院,杨杨对此表示理解。“大城市是很累,不过那里有梦想,就像我现在还是很怀念北京,虽然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回去。我觉得,年轻人也需要停下来休息,而且,生命也是有很多可能性的。”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原文>> ![]() 网页链接 https://3g.k.sohu.com/t/n810605810?serialId=01113709fba1e7a5e572f56b765da33a&showType=news
网页链接 https://3g.k.sohu.com/t/n810605810?serialId=01113709fba1e7a5e572f56b765da33a&showType=news
Imane Khelif在联合国对自己的成长经历作的叙述:
16岁时她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偏僻小村踢足球,因为踢球踢得好,村里的男孩要挑衅她、要打她。她是从这里开始接触拳击的。她爸爸在撒哈拉沙漠当焊工,他不支持女孩学拳击。她靠自己卖旧金属,靠妈妈卖couscous(一种北非主食)的钱,每周去十公里以外的村子训练。阿尔及利亚女孩参与体育的机会是受限的。她想用自己的成绩激励阿尔及利亚的女孩战胜成长中的种种困难。
然后你们这些女性主义者就是这么对她的。就因为她的外貌认定她是男人,不听任何事实,谩骂她,侮辱她,要她退赛,要取消她的成绩,力图成为阻碍一个女性参与运动最大的阻碍。这就是你们的女性主义。
https://www.unicef.org/algeria/en/stories/top-female-boxer-imane-khelif-dreams-gold-inspire-young-people
林郁婷学拳是为了保护被家暴的妈妈。“孝順的郁婷將每次比賽的獎金都交給媽媽、貼補家用;她表示,這四萬元也要獻給辛苦的媽媽。”
然后你们这些女性主义者做了什么呢?
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720309
- infj
- 阴湿圣母
- Green wing
- Mac&Caroline
- 《Bojack Horseman》
- 自我认同是Diane
- 女权
- 女权不是你霸凌的工具
左派:毫无武德的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