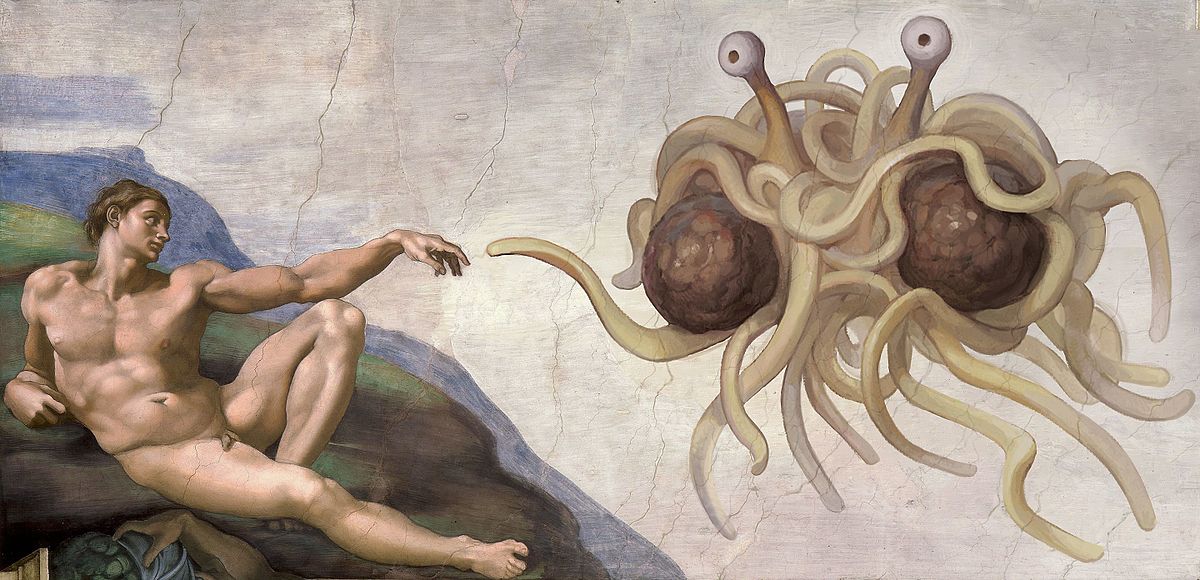博德之门串
笑死我了,逛社区有兄弟:盖尔爆了怎么办?评论区:我把阿斯代伦杀了还能救吗?再结合之前那个把影心上来就刀了的,你们几个真行啊!
我觉得这杯才是草莓奶品系真正的赢者,本频道出现的第一杯冠军,不额外加糖只有草莓和奶融合的味道,不甜,奶味非常纯香,然后大福和奶冻的口感结合得非常好,顺滑柔软,小料的品质太让人感动了,也可以吸到些微的果肉,完全是茶百道草莓奶冻的升升升级版,市面上应该没有哪一款能做得这么好喝,如果想喝草莓奶,点这杯就够了 9.5分 #鸟茶
我真服了,在看巴黎大饭店了,尾花的新店员工分别讲法语、日语、韩语和英语,神经病啊!!!人均语言大师吗?怎么听懂的啊!演一下行不行啊!!!都说法语不行吗!!!这里是法国不许说韩语!
今天参加公司的妇女节活动 panel的一位panelist分享了一个故事。她小时候住在多伦多车程约两小时的地方,附近只有他们一家亚裔家庭。她小时候就一直为和别人不一样而焦虑。她爸爸有些结巴,她会说她爸:“我们已经和别人不一样了,你不要结巴了。”她爸也没有反驳什么。
covid的时候,她的一位朋友想写一本书,收集100个加拿大移民故事。她被邀请采访了她爸。她爸跟她说,很小的时候家里揭不开锅,家里决定派他们家的大儿子(也就是她爸)游到香港讨生活,接济家里。她爸拿着一个轮胎就去游了。游第一次被抓住送回来了;游第二次又被抓住,说如果再被抓住就要被处罚(进监狱之类的?)了。他回来和家人说再被抓住就会被处罚,家人说那我们也没办法,你是大儿子我们只能靠你,那你就晚上游。于是在一个夜晚他第三次出发。他游了好久好久,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也不知道能不能到,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来。最终他游到了香港的一个海滩。从那以后,他就开始结巴了。
既然都在聊跨性别,反正我也无聊干脆来说点什么。
的确,一定是因为有性别区分才会有跨性别的存在。假如世界上没有区分性别,就没有跨性别。但这不代表你不会看到有人想切掉自己的胸或者牛 ——我举个例子,这世界上存在一种人叫 BIID,他们会想要切掉自己的健康的器官,比如手、脚,或者弄瞎自己的眼睛,不这样做就非常痛苦。人脑并不像有些人想当然那样,只有受到社会规训才会想切掉健康器官。我保证哪怕是根本没有任何性别刻板印象,哪怕大家都丝滑接受男的有b女的有牛,那也有“跨性别”的存在,虽然人们可能会把这些人改叫生殖器认同障碍,之类。
任何喜欢说“是因为性别刻板印象才造成跨性别”的,我只能说不安好心。
跨性别现象并不是因为性别刻板印象造成的,许多跨性别在完全不知道跨性别的存在的时候,出现过身体焦虑,即,因为自己身体的发育没来由的感觉到难受,这种身体焦虑根本不是消除社会性别就能缓解的,就像一个人得了抑郁症并不能因为社会不歧视抑郁症患者就不会发病。消除社会性别顶多让他们换个名字,而不是“跨性别”现象从此就不存在了。冷知识,即使是顺性别男性也有人会想割牛牛,真的,就像顺性别女性也有想切卵巢的。
那有人会问:跨性别有没有在追求性别刻板印象?答:有。因为没有办法没有,因为整个社会还在疯狂的拿性别刻板印象去猜别人的性别,并且区分对待。悲观地说,我甚至觉得这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很多跨性别不得不去追求性别刻板印象,这并不是因为跨性别群体有多道德败坏,而是因为这样才能生存下去。更何况,顺性别可以拿出身份证,喊出自己的朋友,证明自己的性别身份,跨性别很难做到。
网友管麻辣哥那个592页的尘白史书叫永麻大典啊啊啊啊啊啊还有汉ml比法典和大义觉麻录。。。。。
上次看到科普说,山根有横纹的话要小心 心脑血管疾病。今天看《有话好好说》(1997),赵本山就有这个特征,查了一下他09年有过很严重的脑出血、也有过心脏不适。。。这才是面相学吧,类似还有耳垂折痕要小心冠心病。这个到底准不准。。。
- infj
- 阴湿圣母
- Green wing
- Mac&Caroline
- 《Bojack Horseman》
- 自我认同是Diane
- 女权
- 女权不是你霸凌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