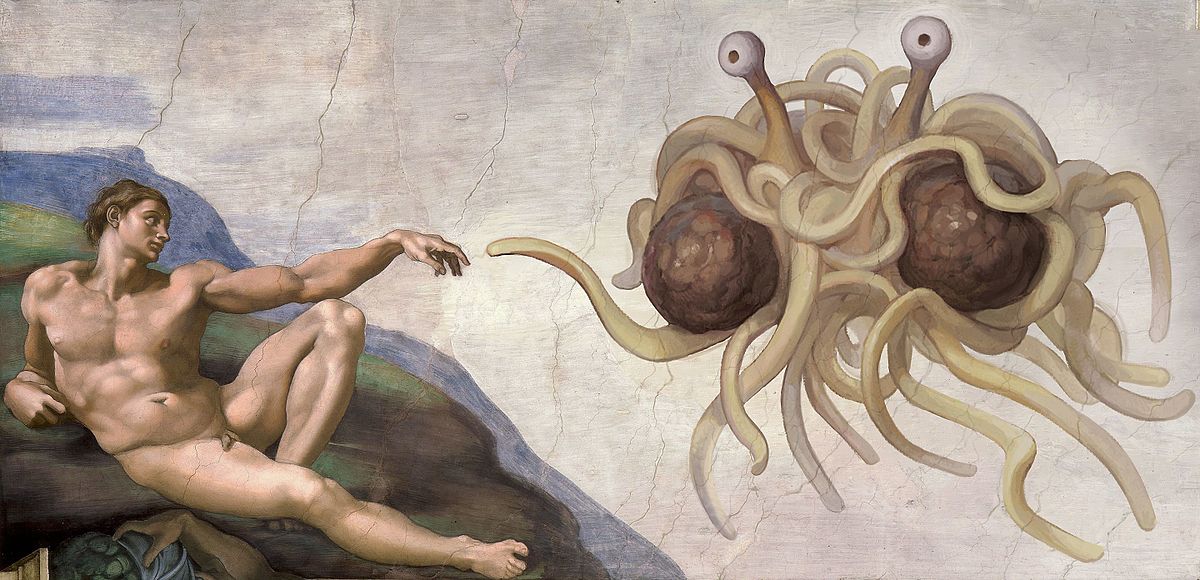Follow
「那信她读完当即烧了,之后那段时间她什么也不说,光坐在那瞧着我哭。
小时候路德来家里玩,我藏起了房间所有钟表。最后还是给老苏菲逮着了。我在卧室踩着一堆书目送他上马车,尽管看不清,可我认定他同我一样脸糊在玻璃上,朝我挥手。
不久前我也妄图把时间藏起来,或者把她藏起来,或者我们从这个地方消失,像两张扑克牌从桌上隐匿,再出现在一位女士的礼帽羽毛后边。可而今我明了,她不阻止我离开的安排,是在等我领悟一切终归徒劳。在她的痛苦之前,我又让步了。
我什么也不问了。我说,你走之后,我不会去中国,也绝不与他们交易。我说,我不会忘了你。她伏案不让注目哭得扭曲的脸。我离她五英尺,不许看她,不能抱她。
等她再抬头,我胸腔随之轰了一声。我读懂了眼神——我不再能知道她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