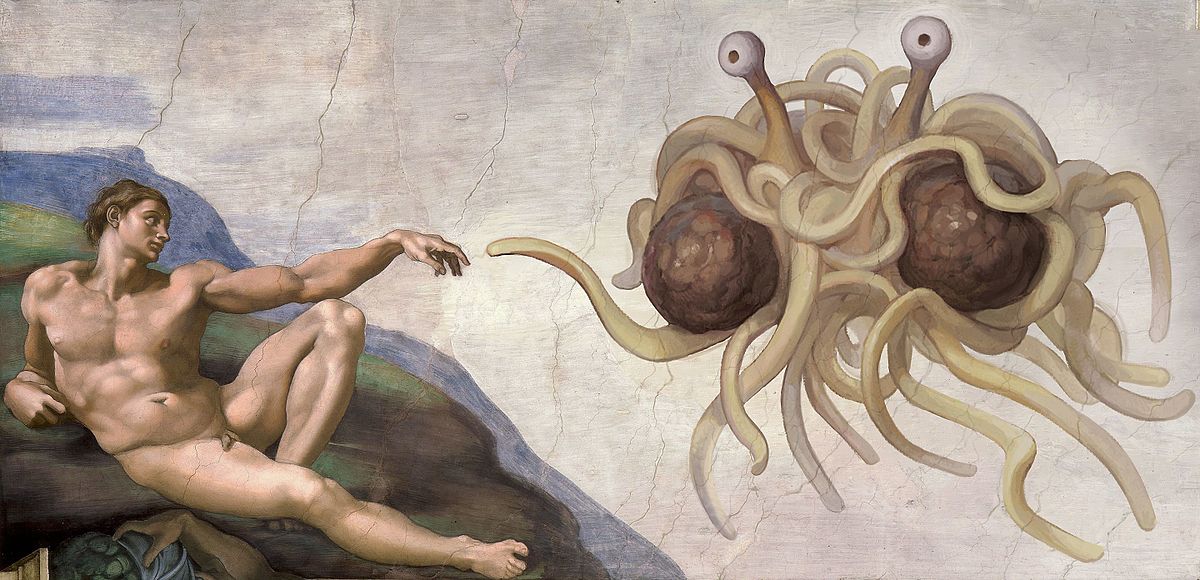Follow
聆听水母
姐姐:那些艺术家需要把他们脑海中的自我与偏执的想法发挥到极致,所以往往对外界要求很苛刻。而我作为工作助理时,就是满足他们、被他们发泄情绪的人。
我:噢……
渐渐意识到那些尽情挥洒的人之外是无数无数工作者给予的托举,正因如此,那个辅助性的世界才会有各种各样能干的人为人所知。也是因为这样,姐姐才能自信地对甲方说,“没有我们的宣传,你也没什么了不起”。在金钱近乎不限量流通的地方,每个工作领域都拥有最为闪闪发亮的角色,他们的骄傲也是对自己能力的认可,对自身名誉的守护——同时也成为社会性的拥趸。
我总是心存妄念,但是在这样的世界也许会被渐渐地融化。曾几何时,我也储蓄着那个高度膨胀的自我这样不断生长,并以为自己会走上某条路。如果我选择了一条岔路,那么,我还能回去吗?都说人生是充满弹性的,但自我的复归……也并不尽然。社会性是某种强奸人脑子的外附本能,铁链勒久了,也许会和血肉黏连在一起。那样的自我还是自我吗?
然而这或许只是一个固步自封的自问自答。个体探索的极致需要外部能量的摄入,停滞不前只会一次又一次地产生同质化的作品和问题。社会化不存在唯一的修行之道,也许另有可以保持警醒的方式。想起九井老师,她对外界的观测又何尝不是一种社会性的极致……那也是个性的一种啊。可惜的是,似乎我生来便比较像图丁兄妹。选择不适合自己的路,肯定是一种打击吧——要想探索这个世界,手段是必须的,对意识警惕心也是必要的,毕竟我们总是在为某种标签而付账的样子。恰如我从前根本不买谷子这次却选择购入,是希望被所爱之物环绕,希望获得一种群体性标志的维护,还是希望观测构成它们的材质呢?或许兼而有之。
一切事无需一定有意义:但是我不想轻易被裹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