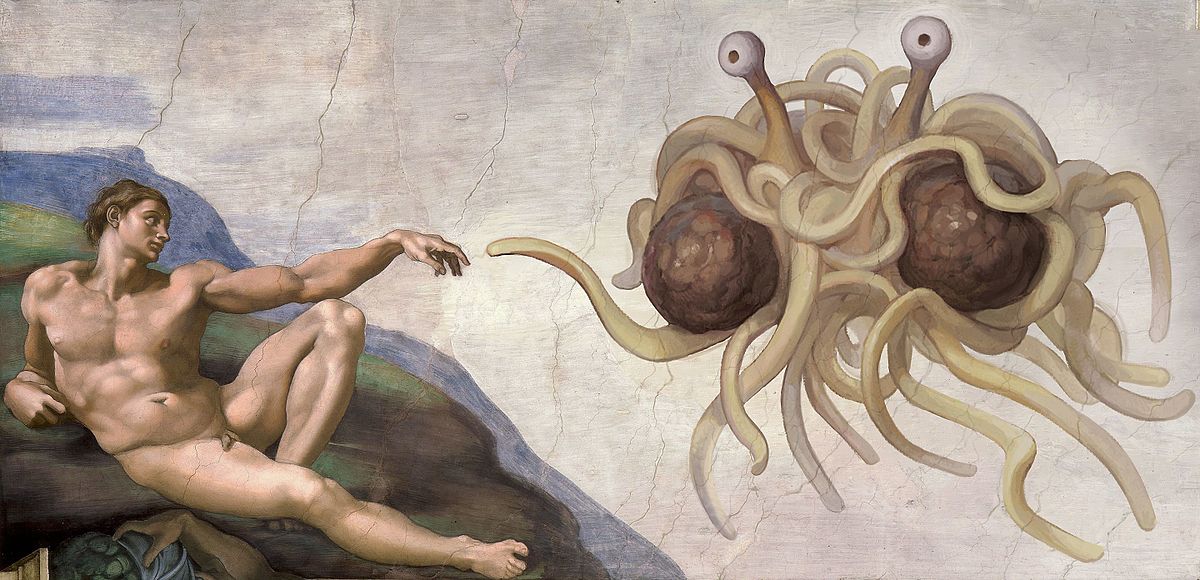我不会写甜文已经到了友说以为我在写梦境,是一出随时醒悟的骗局的程度。不知是我写得不对劲,还是她对我文的印象早定格在悲剧;难说是由于阅读传统还是我读完《人生道路诸阶段》也没解答的那个问题(尽管读的时候我也没寄望于借哲学解决问题)。
我的感知是他始终困于退婚事件,抑或他在反复书写退婚原因以抒发。这里阿克是否喜欢前未婚妻本身不重要了,他陷进一个死胡同:因为我不知何为爱,所以我不能进入爱——如开篇的大学生所言。
有时我也像那个反复诘问究竟何为爱情的青年,「为何围绕该命题的文学作品源源不断,却从未有哲学家探讨什么是爱情」。
我写恋爱会不由自主往悲剧方向走似乎根源于我并未相信爱情,或者说尚未看到一种让我信服的爱情的形态。
我厌恶《一位陌生女人的来信》,首先心理描写并没有给我惊喜,更主要是,她整一个献身实际是通过不断复制过去的自我来构建「我」的过程。她第一次跟作家上楼(之后上床)前的描述是「啊,这是我从小想到大的楼梯」,诸如此类的描述随处可见,她很多时候的注意点并不在作家本身而在过去那个时间点。
写到这重读了《窄门》第七章至结局,忽觉和我以前想的不是一回事。我起先过分放大了阿莉莎更换书架上的书这一节,以为她在他和上帝间选择了成全他,为了让热罗姆不再崇拜她而「自甘堕落」,却又无法接受自己的伪装才郁郁而终。可我现在发现她换书和做家务皆是为了逃避热罗姆……她始终没放弃过上帝,我当时是不是因为《面纱》太在意「偶像坍塌」了,在热罗姆当时的角度看似乎存在这一点,但不多。
那很遗憾,也好在不是。现在人都从关注他人回归到关注自身了,向神灵献祭式的爱情终于不再被歌颂。
另一种形态是,「因为那个人和我很像/有很多共同爱好聊得来,所以喜欢」。不得不提友人拉我看的《花束般的恋爱》,我一直想:喜欢一个和自己很像的人难道不是变相的喜欢/肯定自己吗?此外人类复杂如斯,两个人的交汇处其实很少,假使对于对方身上和自己不同之处视若无睹,实际仍未真的接纳,不过是从对方身上捕捉自我的延伸——就像电影的男女主对于对方喜欢的博物展/热气球并不感兴趣。这里重点在于,我可能不太了解你喜欢的东西,不过我愿意为你去尝试了解——喜不喜欢另说,至少我试过了,而非搪塞或装作感兴趣让对方误会。
至于别的,婚姻,在我眼里已经和找合伙人没多大区别了。你说搭伙过日子过了几十年的老夫老妻,外人又怎知那是撑过了七年之痒,还是财产分割或抚养权之类太麻烦所以凑合着过呢。
就是说谈个恋爱途经无数个滑向悲剧岔口,所以写悲剧性是很容易的。可一路向前能走到什么地方,我至今不知道,至今不会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