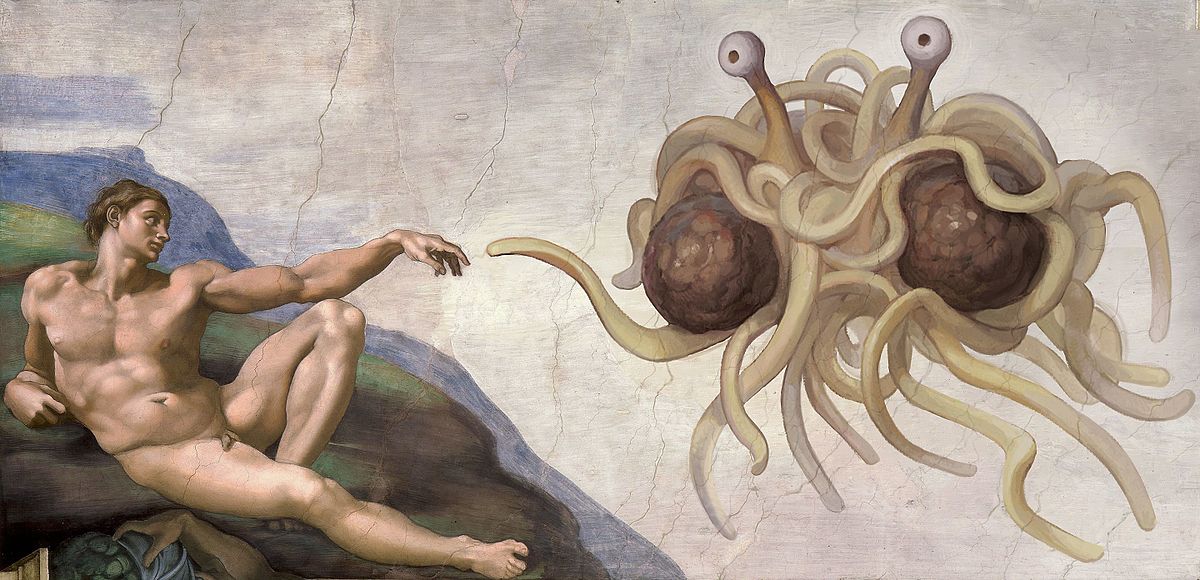护工暂时请假所以跑去精神病院看护我姥姥,这个医院的住院部其中一栋大楼被改成了生活不能自理人(但又不需要治疗只需要有人看护)专属的区域。由于本地是小破城市所以楼也破破的,样子很像以前老上海的弄堂,每个病房的墙皮都旧旧的还有水渍,开着门,看得到里面灰尘遍布的小床。整个楼道里都回荡着护工们坐门口闲聊天的声音,被捆在床上还有力气的老人的胡言乱语,还有更细微的无法组织语言的老人的呻吟。
我姥姥已经完全失能,身体基本只是一副活着的骨架,插了鼻饲管和尿管并且无法动弹,所以我只是躺在一边看书玩手机并且定期给翻身,不过仍然能听到她大张着嘴艰难地呼吸,以及随着呼吸在床上发抖似地摇晃身体,轻微撞击被褥的闷声。
她的儿女几乎竭尽全力,精疲力尽,不能说不是因为充沛深厚的爱和不舍。但徒劳地延长生命不知怎么就变成这样,既不能触及自己,也不能触及世界,实际上已经满足不了“生”的概念范围,唯一的意义大概只在于对其他人来说“没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