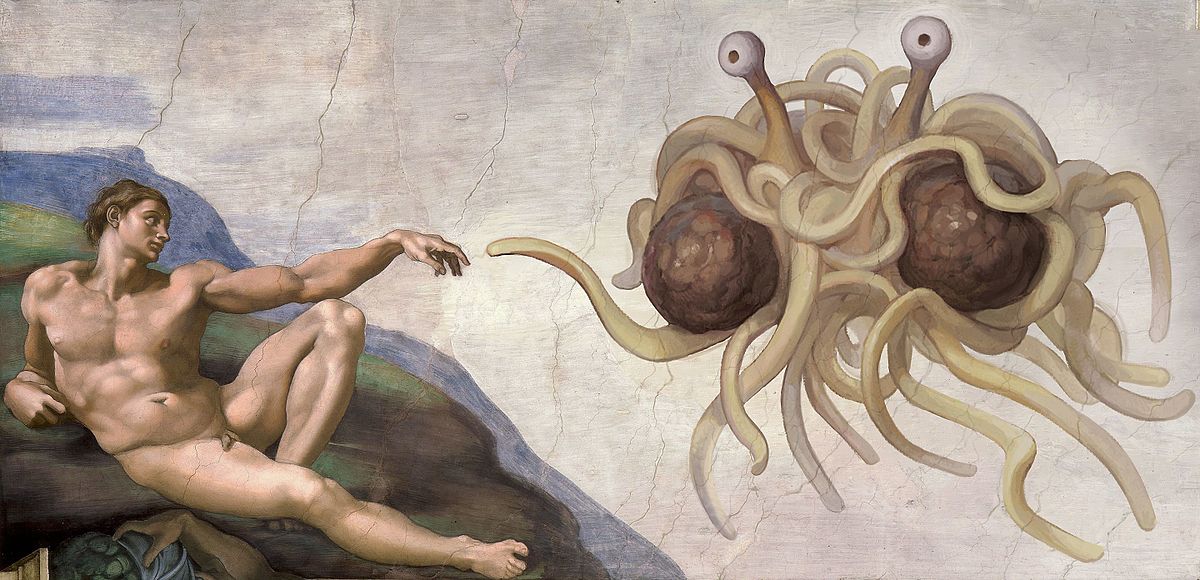“我回顾自己当时作诗的态度,有一句想说的话。那就是,必须经过许多烦琐的手续,才能知道要在诗里唱出真实的感情。譬如在什么空地上立着一丈来高的树木,太阳晒着它。要感到这件事,非得把空地当作旷野,把树当作大树,把太阳当作朝阳或是夕阳,不但如此,而且看见它的自己也须是诗人,或是旅客,或是年轻的有忧愁的人才行,不然的话,自己的感情就和当时的诗的调子不相合,就连自己也不能满足的。”
“所谓“诗人”或“天才”,当时很能使青年陶醉的这些激动人心的词句,不晓得在什么时候已经不能再使我陶醉了。从恋爱当中觉醒过来时似的空虚之感,在自己思量的时候不必说了,遇见诗坛上的前辈,或读着他们的著作的时候,也始终没有离开我过。这是我在那时侯的悲哀。那时候我在作诗时惯用的空想化手法,也影响到我对一切事物的态度。抛开空想化,我就什么事情也不能想了。”
"这个意思,就是说把两脚立定在地面上而歌唱的诗。是用和现实生活毫无间隔的心情,歌唱出来的诗。不是什么山珍海味,而是象我们日常吃的小菜一样,对我们是“必要”的那种诗。——这样的说,或者要把诗从既定的地位拉下来了也说不定,不过照我说来,这是把本来在我们的生活里没有都没关系的诗,变成必要的一种东西了。这就是承认诗的存在的唯一的理由。"
“最简捷的来说,我否定所谓诗人这种特殊的人的存在。别人把写诗的人叫作诗人,虽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写诗的人本人如果认为自己是诗人,那就不行。说是不行,或者有点欠妥,但是这样一想,他所写的诗就要堕落……就成了我们所不需要的东西。成为诗人的资格有三样。诗人第一是非“人”不可。第二是非“人”不可。第三是非“人”不可。而且非得是具有凡是普通人所有的一切东西的那样的人。”
“话说得有点混乱了,总而言之,象以前那样的诗人——对于和诗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物,毫无兴趣也不热心,正如饿狗求食那样,只是探求所谓诗的那种诗人,要极力加以排斥。意志薄弱的空想家,把自己的生活从严肃的理性的判断回避了的卑怯者,将劣败者的心用笔用口表达出来聊以自慰的懦怯者,闲暇时以玩弄玩具的心情去写诗并且读诗的所谓爱诗家,以自己的神经不健全的事窃以为夸的假病人,以及他们的模仿者,一切为诗而写诗的这类的诗人,都要极力加以排斥。当然谁都没有把写诗作为“天职”的理由。“我乃诗人也”这种不必要的自觉,以前使得诗如何的堕落呢。“我乃文学者也”这种不必要的自觉,现在也使现代的文学如何与我们渐相隔离呢?”
“真的诗人再改善自己、实行自己的哲学方面,需要有政治家那样的勇气,在统一自己的生活方面,需要有实业家那样的热心,而且经常要以科学者的敏锐的判断和野蛮人般的率直的态度,将自己心里所起的时时刻刻的变化,既不粉饰也不歪曲,极其坦白正直的记录下来,加以报导。
总之,假如不是如上文所说的“人”,以上文所说的态度所写的诗,我立刻就可以说:“这至少在我是不必要的。”而且对将来的诗人来说,关于以前的诗的知识乃至诗论都没有什么用。——譬如说,诗(抒情诗)被认为是一切艺术中最纯粹的一种。有一个时期的诗人借了这样的话,有如说蒸馏水是水中最纯粹者一样,可以作为性质的说明,但不能作为有没有必要的价值的标准。将来的诗人决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同时应该断然拒绝对诗人的毫无理由的优待。一切文艺和其他的一切事物相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只是自己及生活的手段或是方法。以诗为尊贵的东西,那只是一种偶像崇拜。”
“此外,诸位对于想把事变成新的东西,太热心了,是不是反而忽略了改善自己和自己的生活的重大事情呢?换句话说,诸位曾经排斥过某些诗人的堕落,现在是不是又重蹈他们的覆辙了呢?诸位是不是有必要将摆在桌上的华美的几册诗集都烧掉,重新回到诸位所计划的新运动初期的心情去呢?”
——石川啄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