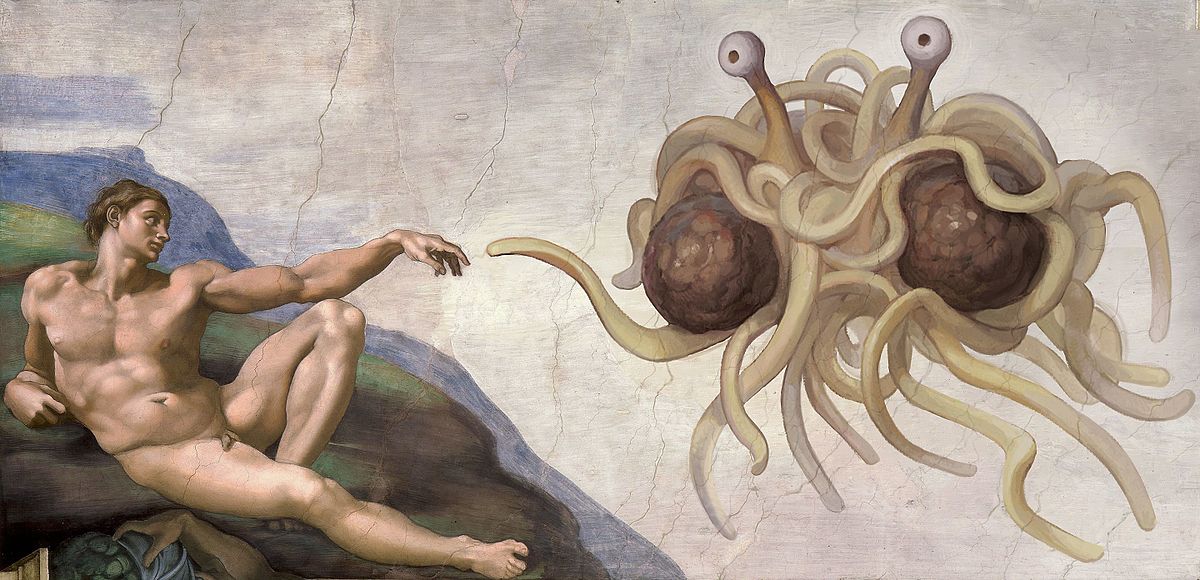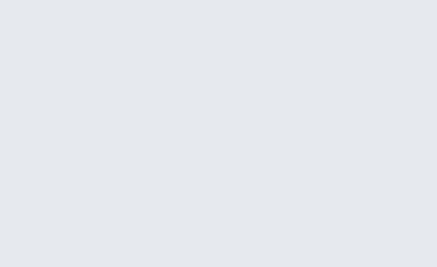
之前跟一个非常敏感并且有抑郁的朋友聊天。我观察到,我和她对时间的感知是不同的,虽然不一定因为她的抑郁。她只需几十分钟,千头万绪很快就长起来叠起来转起来了。我听她说话,好像用 x10 倍速度看动作片,场景快速切换,信息量、情绪密度极大。她自己也因此常处在透支后的兴奋和疲惫里。当她说“我最近很好/糟”,她的最近指的是一天甚至一小时前。而对多数人来说,最近的时间尺度是按周和月来计算的。
这两年我也有这种时间度量衡的失准感。尤其是进入动荡年代后,总觉得变化常在朝夕之间。回想自己去年的事,都像偶听旁人十年前的旧闻。每天被困在不断做选择中,总是一个决定还没捂热,又开始下一个。人人默认蹲踞式起跑状,就等枪响,开始一场悬崖边缘的百米跑。
信息过载和政局动荡肯定是部分原因。但在文艺青年念叨的从前慢和反贼自嘲的推背感之外,我还被某种广阔又陌生的文明消逝感包裹。一些价值,一些生活方式,永远消失了。
看到法国高考会考09-17年的作文题,感到震撼,一是与某国之间的差距,二是命题的开放性和哲理性确实超乎想象,每一个问题都是那种似乎需要看完几本哲学著作打坐冥想好久才能下笔的论题,我不禁想经过这样的思考试炼出来的学生,会拥有怎样的深度呢。老实说我看到这些题目是完全没有思路的,很多论点我根本没接触过,怎么展开,怎么论述,怎么开头怎么收尾,完全没有头绪。比如“无尽的欲望是人的本性吗?”、“我们应当用认知来论证吗?”、“为什么人需要寻求认识自己?”、“人活着是为了幸福吗?”、“我们能挣脱自己的文化吗?”、“人们能否凭道德行事而不受政治倾向影响?”,甚至是“没有国家我们会更自由吗?”
它们是和“你是谁从哪来到哪去”类似的终极问题,这些问题让人想码下来用一生的时间好好思考,作为已经脱离校园的人,我不去评价作为考试题它们合不合适,我仍然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思考这些问题,它们是人观念的成长过程中很好的母题。
今天一边运动一边听马世芳“耳朵借我”电台的《六四三十年祭》节目。大学的时候还会在墙内发几张《颐和园》的剧照。而今天试图说些什么想想都欲言又止。但是所有恐惧都不及如此精确地知道我周边有认识的人也在长期的打磨训练中被塑造成为了这个机器的一个精密零部件。我不由自主沉浸在这样的恐惧中。总有人自发地加入这个系统,也许其中会有人将枪口抬高一寸,但是我不相信它。
很难想象,我们竟然曾经有过谷歌,脸书,电视上的日漫和美剧,instagram,未删减的云图,可以上映LGBT影片的电影节,骄傲节,Wikipedia,Uber,Linkedin,Airbnb,亚马逊,iTunes,Kindle……而没有哪一代人能够感受到我们这种生活被一层层抽空和剥离的无力。2019,进入另一个平行时空。
毋忘六四
找回手机里19年六四晚会的相片,那年正值三十周年,有超过180,000市民参加晚会,参与人数为历年最高。人群挤满维园六个足球场,手中的烛光数不胜数。所有人沉默不语一同祈祷,用自己的方式缅怀同胞,那是我印象最深的六四悼念记忆。那次烛光晚会出席人数破纪录,原因之一就是要为6月9日的大游行造势,而超过一百万人参加的大游行也拉开了反送中运动的序幕。
三十年前先辈们坚持过,三十年后港人仍要为现在抗争,但两次运动最终都因中共镇压而结束。八九民运本应该成为改变的起点,人民已选择要迈向民主体制,但是中共拒绝接受反而令它成为了独裁统治下的悲剧,又在三十年后重蹈覆辙。我们没有理由不去记住这段历史,悼念六四本身就是一种延续和抗争,为公义呐喊与极权对抗。
过去影响现在,而现在又决定着未来,政权希望得到沉默,因为89民运的生命力还存在于记忆中,有着无法撼动的力量。而作为公民,良知告诉我要铭记六四,在最绝望的境地里,我仍愿意相信所有的勇敢与执着会令公义重见天日,希望的种子仍将冲破障碍生根发芽,民主之花终有一日会在广阔土地上自由盛开。
六四33周年
点燃、举起、不灭🕯️